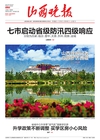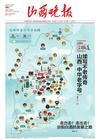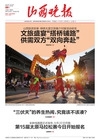《返璞归真:考古纠错的中国史》,以考古成果筑牢“疑古”根基
该书话题范围上至传说时代,下界明清时期,吸取了近百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对考古所证伪的史籍所载32宗中国历史问题和事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用确凿的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对其来龙去脉都做了详尽的叙述和说明,并分析了这些历史事件在文献记载中出错,以及为什么会出错等情况,将考古学成果转化成普通读者容易接受的通俗读物的形式,匡正了历史讹误,还原了历史的本真面目。
看李琳之新著《返璞归真:考古纠错的中国史》的几个章节标题就有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不读不快之感。诸如:中华文明起源并非“一元中心”;距今五千年前后不是黄帝时代;三代大同社会遭遇尴尬;出土金文显示:周厉王是一代枭雄;“烽火戏诸侯”名不副实;陈胜吴广起义“失期当斩”是托词;秦阿房宫根本没有建起来;蔡伦不是造纸术的发明人;等等。他的系列新书,以最新的考古成果为中国历史界的新“疑古学派”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中国史学界发起疑古思潮开其先河者是顾颉刚先生。顾颉刚先生考辨古史的根本意图是考察古史学说或观念的流变,以解释旧有古史系统是如何构成的,从而发现中国古史中的不实之处。李振宏发表在《齐鲁学刊》2020年第2期的《顾颉刚疑古史学的现代价值》一文中对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作了详细的介绍与积极的评价。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顾颉刚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在疑古批判精神激情澎湃状态下,顾颉刚提出大禹不是真实存在的人,而是一条虫的论断。根据大禹最早的出处,他最早在书籍中发现,大禹是以一位天神的形象出现的,等他再翻到下一本书时,大禹又化身成为了人间帝王,随着后来一本接一本古书的出现,大禹的形象在这些书籍中日趋丰满,成为了今天看到的样子。由此,大禹的来源成谜,于是他便从禹这个字本身入手,由此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禹只是一种动物,一条虫,是古代铸造在九鼎上的一种动物。九鼎在古代代表天下,是所谓取天下之青铜冶炼而成,与后世的传国玉玺地位相当,由此,其身上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自然会很多,经过世代的以讹传讹,最终演变为真正的帝王,自然在情理之中。
顾颉刚的疑古史学,体现出的是学术的批判性。但是其缺陷是仅仅从历史文献的考察出发的,而缺乏考古成果的论证,因而其基础是松软的,不坚实的,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而他的这一重大缺陷被李琳之先生给弥补了。这些个21世纪20年代的新“疑古论”,远远超出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20世纪20年代的疑古派。而且21世纪20年代的新“疑古论”是建立在100多年来的考古发现的新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文献文字的考证之上。其坚实的基础是令人不得不信服的。
顾先生提出的推翻非信史的四个项标准,李先生用考古成果完全做到了、坐实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与(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这一、二两项标准在书中第一个专栏中有鲜明的体现,如“中华文明起源并非‘一元中心’”“南方文明起源进程不迟于北方”“石峁古国改写‘西戎’文明史”“石家河古国改写‘苗蛮’文明史”等;(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李琳之的上古系列著作都做了详细的阐发,他不仅仅是“疑”,更重要的是“建”。他的“史前中国四部曲”(《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晚夏殷商八百年》和《何以华夏》),就是利用考古学成果重新构筑的目前所见唯一一套完整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第二专栏中的“三代大同社会遭遇尴尬”“圣王治理下的西周也施行人殉制度”,就满足了这项标准。顾先生地下有知,应该心满意足昂首庆幸了吧。
这里仅以《返璞归真:考古纠错的中国史》一书中烽火戏诸侯与秦阿房宫根本没建起来为例,来看看他是如何利用考古成果为自己的论点作论证的。
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误以为历史上确有这样的荒唐事。然而李琳之却认为并无此事。他的论证是,指出考古成果说明西周时代并没有修筑烽火台遗址的证据。烽火台设施的出现是秦汉之后,而且就目前考古所见,都是发现在偏远的边境地区。就此一点,就证伪了烽火戏诸侯存在的可能性。书中还对司马迁之编造烽火戏诸侯故事的认知观念及其来源的详细分析,可谓在情在理,在此不提。
秦阿房宫历来被用来证明秦始皇的荒淫无耻、横征暴敛的恶政。而李琳之以考古资料论证了阿房宫(前殿)面积并不大,夯土基址东西长约1270米,南北宽只有426米。考古人员在发掘中还发现,阿房宫(前殿)遗址的表土层之下为扰土层,就是处于耕种层和文化层之间的那层土。扰土层下是汉代至宋代的文化堆积层,再往下就是阿房宫(前殿)基址。其间没有发现与秦汉宫殿建筑遗址相关的墙体、壁柱、础石、散水、地面、窖穴以及给排水设施一类遗迹。这种情况意味着,阿房宫(前殿)只是打了个地基,地面上的建筑并没有建起来。
为了验证“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真实性,考古人员在阿房宫前殿遗址的考古勘探试掘发掘中,不放过任何与火有关的蛛丝马迹,但在其间根本找不到任何经过火烧的痕迹。确凿的考古成果证明了后世传说的阿房宫根本就不存在。
马克思说他的学说是批判的、革命的,他把怀疑一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怀疑,是理性思考的开始,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没有怀疑,就没有探索,就没有研究。疑古,疑今,疑成说,疑经典,思想才能解放、学术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这在李琳之先生著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以本书和《史无记载:考古发现的中国史》《传说有据:考古证实的中国史》两书共同构成的李琳之“考古改写中国史”三部曲,事实上是在“疑”的前提下,修正、补充、丰富和完善了既有的中国文本历史,这正如出版方在第32届书博会上举办的李琳之“考古改写中国史”系列新书发布会,将“百年考古,重新书写了一部怎样的中国史”作为主题,其意义不言而喻。
武高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