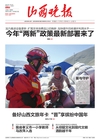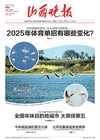著名汉学家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星象学的作品《中国早期的星象学和天文学》节选——
天文学始于陶寺
《中国早期的星象学和天文学》
[美]班大为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在该作品中,著名汉学家班大为阐述了星象学如何从一开始就塑造了中国文化,以及它如何影响中国的艺术、建筑、历法、神话、政治和军事决策等。本书研究了考古发现、古典文献、铭文和古文字等广泛的资料,记录了从新石器晚期到清朝晚期天文现象在“天朝”发展中的作用,阐释了天文现象如何深刻地塑造了古代中国文明。
在历史记述和传说中,从山西省西部的汾河至黄河陡然向东转向并经过洛阳的区域,便是中国第一个可能的朝代夏的核心地带,夏从公元前约1953年至前1560年统治着中原地区的西部。对新石器晚期二里头城市遗址及其对华北大范围文化影响的研究,已经证实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国家的形成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1959年以来对二里头的几十年研究已经证实这是一个高度阶级化的社会,城市中心用坚实的城墙围绕,精英统治阶层,宫殿式建筑,奢侈物品,精致的宗教仪式,早期的青铜器工业,所有这一切都由大量的农产品剩余和贸易网络维持着。
直到最近,较不为人所知的陶寺才走进人们的视野,这个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城市,位于山西境内汾河河畔的平阳地区(北纬35° 52'55.9″,东经111°29'54″)。陶寺包含至少4个史前城市遗址,这些城市从公元前约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在该地点屹立了500到600年,鼎盛时期扩张至周围约3平方千米范围。陶寺最初发现的时间约与二里头相同,即20世纪50年代晚期,但直至二三十年之后,平民住址和一个贵族公墓才发掘出土。迄今共发现1300多座墓葬,其中包括陶寺早期的统治者们,表明前王朝时期出现过一个非常大的王国,其贸易触及非常遥远的地点。该遗址的断代和地点,均与后来向王制早期的转变保持一致。
从1999年至2001年,考古学家发掘了一个大型的陶寺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夯土围城遗址。城址约呈长方形,总面积为28平方千米,这一发现使得陶寺成为中国目前已知的史前最大围城。除大量的夯土建筑基址、墓葬、窖坑等外,考古还发掘了一个铜钟、精美的玉器、斑斓绚丽的彩绘陶器,以及社会贫富分化悬殊的证据。更令人激动的是,书写符号的发现,使人联想起500年以后商代的甲骨占卜文,很有可能这一时期已经使用文字,只是写在易腐朽的载体上,没有留存下来。
直至没落,陶寺晚期在文化上已经与同时存在约一个世纪的二里头早期阶段一样成熟。而且,陶寺具备二里头文化的前述所有特征,即便发展可能有些许落后。考古研究显示,陶寺中期约公元前2100年左右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早期的小城镇转变为大型的城市中心,后者在规模上是以前的5倍。陶寺成为龙山文化前王朝时期最大的城市,贵族众多,宫殿规模史无前例。尽管存在很多争议,通过一些元素——时间、地点、文化水平,一些中国学者已经确定陶寺是中国前王朝时期的英雄人物——尧帝的都城。传说和历史都提及,尧征服了一个称为陶唐的方国并在平阳建立首都。
进一步向前审视所谓较小的方国,陶寺的征服统治者带来了全新的象征着遥远东边的龙山文化的文化产品——雄伟壮丽的宫殿,富丽堂皇的墓葬,轮制陶器,模制技术,新的陶器器形,彩绘装饰图案,铜器制造,骨卜,玉漆器物和书写符号。墓葬中发现的与众不同的手工制品证实该地区与遥远的诸如东南方800公里之外的良渚等其他文化存在贸易往来。但是陶寺人民也从事一些以前中国新石器晚期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通过太阳观测来进行仪式化的天文活动和纪时,这一创新使尧的统治至少自公元前第一千纪早期起就声名远播。虽然在这一早期中国北方的这一创新史无前例,但它并不稀奇。50年前徐复观写道:但我们只要想到古巴比伦在天文上的成就,则中国在唐虞时代已积累有了若干历象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在政治上是有一定的人加以传承,可以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因而保存了下来,又有什么稀奇?
这里我们将集中探讨陶寺的考古遗迹。
2003年在陶寺中期大城的东南围墙旁边发现了一个围城遗址(IIFJTI),包含夯土筑成的三层同心建筑,总面积超过1400平方米。该建筑被复原为一个三层坛台。第三层,即坛台的顶层是一个半圆平台。这三层梯台临近一个贵族墓地,显然被用作祭祀供奉。坛台上有一组弧形夯土墙,面朝南-东南,残留的地基遗迹上排列有12个间隔均匀的凹槽,间距约1.2米,凹槽宽25厘米,目前仅深4-17厘米。对这些凹槽的分析显示凹槽之间突起的夯土很可能是形状约略一致的土柱的遗迹,其横截面为长方形或梯形。考古学家从结构上推测弧形土墙应最先建好,随后以规则的间隔切割完成这些凹槽。
由于墙的弧度接近全年东方地平线上的日出方位角范围,考古学家认为这个平台可能被用于观测日出,同时具备祭祀和天文功能。站在梯形平台中心,透过基墙中的狭缝进行观测,考古学家发现它们大多数朝向东-东南方向的塔尔山山脊。狭缝E2-E12的方位角范围与冬夏至之间太阳沿地平线的运行轨迹一致。一开始基于计算和实地观测的分析认为狭缝很可能被设计为可以在两至等特定日期观测太阳在地平线上的升起。也就是说,这一遗址被认为是一个祭祀坛和太阳观测台,从而结合了自从公元前第一千纪早期起在文献和铭文中均提到的称为“灵台”的神圣建筑的性质。
何驽带领的考古团队,在2003-2004年对这个半圆平台进行了发掘,发掘工作假定夯土台基的设计意味着它可能存在与日出观测或太阳祭祀有关的应用。考古队从平台圆弧的计算中心对半径和角度进行了最初的测量,随后模拟日出观测。观测工作通过制作一个与基墙缝隙各方面尺寸一致的铁架框,并在各凹槽上轮流移动这个铁架以确定太阳何时在铁架框中升起。这些田野调研和长达一年的观测完成之后,才在一个以前未曾发掘的堆土台下发现一个圆形夯土台基。这个圆形小夯土台基的中心,有一个直径25厘米的夯土芯,明显地标记出原始观测点的精确位置。该观测点离这个台基的计算中心仅相差4厘米,强有力地支持了有关其功能的假说。武家壁和何驽计算了公元前2100年太阳两至时在陶寺的日出点,证实了这一台基很可能用于太阳观测的假说。进一步与天文学家进行讨论后,考古学家认为,最初的测量和观测工作应该在新发现的观测点、应用更高精度的仪器重复进行。这一工作在2004-2005年完成。
对观象台的布局进行研究,可知该结构可能是如何建造的。弧形夯土墙基在冬至点位置进一步向南延伸,而在北端的夏至点位置变短,这显示出一开始建造者可能没有很好地掌握相应的方位角范围。最靠近冬至点的狭缝(E2-E5)指向最精确(从标记中线的黑点可知),这表明它们以冬至点为基准,其他的狭缝均匀排列,沿东北方向每个间隔约1.2米(新石器时代的单位?),一直到中点E6处,累计的测量误差导致此处的位置与中心观测点严重偏离。也许,六个月以后才认识到无法观测到夏至时太阳在东北方向的升起,因此额外增建了狭缝E11-E12,但是由于地点的限制,这一附加建筑不得不与主体割离,并远离中心观测点。狭缝E11-E12奇怪的地点和特征,很可能源于其建造时间与E1-E10不同。而且,该结构的设计以及12个间隔均匀的狭缝,显示出不了解或没有意识到太阳在四季沿地平线升起的日常变化。有趣的是,弧形可能反映出当时认为天空是圆形的,因为一个直线的队列同样可以满足这一需求。除确立两至点和回归年长度以外,很难理解这一布局有任何历法功能。然而,灵台展现的反复试验过程和缺乏一定的熟练性显示出技术上与陶寺新石器晚期文化水平的“适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