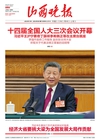大同市平城区文瀛南路北魏墓地
见证迁洛前后平城最后的辉煌
发掘单位:大同市考古研究所项目负责人:靖晓亭
大同,古称平城,作为北魏都城有97年之久。
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孝文帝假借南征的名义,率领群从百官、步骑百余万浩浩荡荡从平城出发,趁机定都洛阳。太和十八年(494年),这场迁都之旅正式完成,平城时代也随之落幕。
2024年,大同市平城区文瀛南路发掘了百余座北魏墓,年代从太和九年(485年)至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为人们了解孝文帝迁洛前后的历史提供了资料,见证了平城最后的辉煌。
地域与人群来源属性特征明显
2024年4月至11月,为配合建龙央玺房地产开发项目,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位于大同市平城区恒安街与文瀛南路交汇口西南发掘了164座墓葬,其中北魏时期墓葬120座。此次发掘自2024年5月13日开始,至11月2日结束,历时近六个月。
据文瀛南路北魏墓地项目负责人靖晓亭介绍,与大同此前发现的其它北魏墓相比,目前这个墓地的规模最大。该墓地西侧、北侧墓葬较少且分散,东南部墓葬则分布密集,整片墓葬呈由东南向西北扩散的趋势,此外,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曾于2021年、2022年分别在该地块东侧及东南侧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工作,推测该处墓地可能位于某一大片区墓群的西北边缘。“包括曾经发掘的司马金龙墓,也属于这一大片墓群,它在墓群的东南方向。”靖晓亭说。
该墓地墓葬分布比较密集,但同时期墓葬却无打破关系。7座东西向北魏墓全部位于大干渠东侧,位置相对独立且集中分布于发掘区北部。其它113座皆为南北向北魏墓,多位于发掘区南部,且分布规律,排列成行,说明该墓地的使用有着合理的规划,依此推断聚葬习俗应该相当盛行。
不同于一般的家族聚葬,该墓地是以地域和人群划分,实际上就是一个来自各个地方的多人群聚集的一个公共墓地。出土的墓铭砖及墓志上,有各种姓氏,包括司马、崔、高、谢、张、黄、前、王、静等,而无同一姓氏,地望有定州高阳易县(今河北易县),长安(今陕西西安),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等。M15崔寄奴墓与M138高謢墓南北排列且均来自定州高阳易县,而非同一姓氏,再加之M157所出墓铭为高阳太守谢还香,说明该处墓地家族性质不明显,而是地域与人群来源属性特征明显。
“这些姓氏都是汉姓,没有鲜卑姓,推测他们应该都是从全国各地迁至平城的外来人员。”靖晓亭介绍,平城人口最多的时候有150万人,北魏定都平城以后,吸引了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地区的各类人群在此生活。这些人中,有征服的各地官吏、能工巧匠们,还有大批的宗室、高官和富户,他们从各地迁至首都,或从旧都迁至新都一带,“而且很多都是大规模的迁移,这个墓地中有墓志的,一般都是迁移小分队的首领”。
胡汉文化、南北文化相互交融
北魏时期的120座墓葬,包括砖室墓59座,土洞墓57座,竖井墓道侧室墓1座,竖穴土坑墓1座,瓮棺葬1座,沟(墓葬未完工)1条,共计出土北魏时期文物587件(套),包括陶器、瓷器、石器、铁器、铜饰件及若干金、铅饰件等。
北魏是民族融合与交流的重要时期,从这些墓葬的葬俗及出土器物上,可以发现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的证据。比如,有20座墓葬出现随葬整只动物的现象,以牛、马、羊为大宗,仍旧延续着大同地区北魏墓葬随葬动物的习俗,有鲜卑或匈奴遗风。
M63出土的一件石枕,正面和背面都是双龙缠绕,是典型的汉文化因素;侧面两边都是站立的人物形象,为带有西域特点的外来人口;底部是母狼喂小狼吃奶的画面,体现舐犊情深,是明显的草原文化因素。这件石枕是目前发掘的众多北魏墓中第一次出土的石枕,此前在大同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都没有发现过。
在出土器物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M29、M42、M52、M82出土的四块瓷片可拼接,拼接后的器型为龙柄瓷器,与此前北齐娄睿墓出土的龙柄鸡首壶相似。靖晓亭介绍,从风格特点来说,这很明显是南朝的瓷器,北朝没有那么大瓷器,而且现在大同还没有发现过北魏的瓷器,瓷器一般都是从南方来的。这件器物出土时已经碎了,至于为啥会出现在四个墓中,还能拼在一起,这一现象仍需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墓中还出现了佛教元素。M99出土了一件陶瓶,被认为是佛教的法器净瓶,与云冈石窟菩萨造像手持之物相同。这类器物,一般出现在僧人或者信徒的墓里。
出土文字为多重历史提供佐证
该处墓地出土多件北魏时期墓志或墓铭砖,文字性的东西较多,年代最早的为太和九年(485年),最晚的为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未发现其它年号,由此判断该处墓地使用年代为北魏迁洛前后,为大同地区北魏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新的资料。
其中,崔寄奴墓志的发现有重要意义,其一,“奴”字不宜入正名,而历史上南朝刘宋皇帝刘裕小名也叫刘寄奴,因为出生贫寒被寄养于他家,而与其相距不远的M8墓主为张奴,且两座墓规模都较大,再结合以前所出的白兵三奴铜鍑,有可能“奴”字在北魏时有着特殊的意思和象征性质。经初步研究,靖晓亭认为名字中带“奴”的人应该和皇家关系比较大,是皇家把他们养大的。崔寄奴的墓志显示,他的官职是内行,也就是皇帝身边贴身的仆人。张奴的墓志虽然没有记载,但他应该也是皇宫里面的人。该墓志中所说的“其墓田位于京城东之南十五里”,为探寻北魏的城郭范围提供了准确的参考。
此外,崔寄奴墓志的书写方式和体例也与以往发现的北魏墓志不同,尤其是最后,“后人不得妄认”,以往此类书写语气多出于后世墓葬,为研究此类墓志的源流问题提供了研究价值。以前发现的北魏墓志规格多为圆额方底、圭形带座,但崔寄奴墓志是长方形的,它是从砖铭到圭形墓志碑过渡阶段的一个代表。
司马元伯墓铭砖正面记载其爵位和官职,为温县子、建威将军、泰山太守,与史书同,而葬于太和十六年(492年),且官职多一领晖侯,有补史的重要价值。背面的墨书已漫浸不清,但依稀可见“东海公”字样,与史书记载其袭其父司马天助东海公后被降为温县子符合。史书记载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实行爵制改革,开始推行实封的王爵、开国爵与虚封的散爵并行的爵位制度。《魏书·孝文帝纪下》记载:“(太和十六年)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这说明司马元伯病故时正处于这一改革施行期间。
该墓地的北魏墓葬被盗严重,且土洞墓也有被盗情况。部分墓葬人骨仍保留着被拖拽的姿态,推测该处墓地部分墓葬在下葬不久后即被盗掘。“以往发掘其它墓,砖室墓十墓九盗,但是土洞墓被盗得很少,因为比较危险,盗墓者也不敢动。但是这个墓地不仅所有的砖室墓都被盗了,土洞墓都被盗,只有一些小型的土洞墓没有被盗,说明还是埋葬的规格比较高。”靖晓亭说。
因为早期被盗了,墓中不多的壁画也被破坏了,在M63和M5发现有壁画,仅剩少许花草和帷幔图案,已由云冈研究院的壁画保护中心揭取修复。
目前,发掘工作已结束,原址已回填。该墓群的发现,以丰富的墓葬形制和文物遗存,串联起平城时代的尾声,为研究北魏迁都洛阳前后的社会变迁、文化融合及丧葬习俗提供了实证。
山西晚报记者 南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