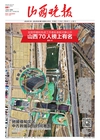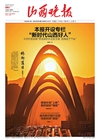传家修身,以“俭”为宝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千古传诵的《悯农》一诗,以极为朴素的言语表达了中华民族反对浪费、推崇节俭的风尚。纵观历史,从传家守业,到立德修身,再到安邦治国,节俭始终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精神内涵。
古人云:“富不过三代”,究其原因,则多半在“奢靡”二字。白手起家之人筚路蓝缕,深知创业维艰,故能克勤克俭;而纨绔子弟坐享其成,耽于享乐,终致家业凋零。南宋叶梦得直言节俭乃是“守家第一法”,主张“日用奉养,宁使家有赢余,毋使仓有告匮”。清代蒋伊给家族立下严规,“不得从事奢侈,暴殄天物。厨灶之下,不得狼籍米粒。下身里衣,不得用绫纱。”这些训诫,实为家族存续奠定了重要生存智慧。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古代家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主要在家庭内部进行,如何合理安排用度成为治家的关键。司马光强调“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清代靳辅《庭训》也认为“治家莫要于俭”,提倡依据家庭人口和衣食用度,量入为出,而至于堂室、服饰、器用诸类,则概从俭朴。张英《聪训斋语》还提出将一年资金划为十二股,每月支用一股,月底若有赢余便积攒起来,既可应对饥荒,又能周济乡邻。这些精打细算的财务规划,为传承家业编织了一张经济安全网。
因此之故,节俭成为教育子孙的重要内容。明代吴麟徵《家诫要言》称“治家舍节俭,别无可经营。”《廷尉公训约》强调“凡一切度用,须要省约,不事奢华”,如此方能衣食有资,日用无亏,家业隆起。清代《丰川家训》认为教育子女的第一件事就是“戒其虚浮,禁其奢侈”,奢侈不禁,必然导致荡业败产,困顿流离。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反复叮嘱子侄“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希望他们谨守俭朴之风,切忌贪爱奢华。
需要注意的是,节俭并非单指资财用度的节制,它还与修身立德直接相关。《左传》有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诸葛亮《诫子书》称“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将节俭从生存策略升华为道德修行。明代《庞氏家训》把“孝、友、勤、俭”奉为“立身第一义”。《聪训斋语》认为一切事情均宜节俭,饮食俭可养脾胃,嗜欲俭可聚精神,言语俭可养气息,交游俭可择友寡过,酬酢俭可养身息劳,夜坐俭可安神舒体,饮酒俭可清心养德,思处俭可蠲烦去扰。高拱京也指出俭有“四益”,即养德、养寿、养神、养气。
节俭绝非锱铢必较的吝啬,而是对礼仪的克制和对性善的尊崇。颜之推强调“施而不奢,俭而不吝”;陆游主张“饮食但当取饱”,却不忘待客之礼;靳辅认为“俭非鄙吝之谓”,接人待物仍须“礼貌相待,施报得宜”;高攀龙倡导省下酒宴一二品、馈赠一二器、衣服一二套、长物一二件,以为济人急难之资。节俭当中蕴含的“厚薄相宜”的智慧,恰是中华文明真、善、美的生动注脚。
节俭不仅关涉个人、家庭,还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早在先秦时期,墨子便警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司马迁在《史记》中亦指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於节俭”。回顾历史上延续时间较长的朝代,莫不是把提倡节俭作为治国的重要方略。唐太宗以隋炀帝奢靡亡国为镜,采纳魏征“戒奢以俭”的谏言,开创了贞观之治。雍正帝大刀阔斧整顿吏治,严惩贪污腐败,为康乾盛世奠定基础。“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一语道破了家国兴替的经验教训。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近年来,从提倡“光盘行动”,反对餐饮浪费,到大力整治畸形“吃播”乱象;从公布施行《反食品浪费法》,到“零废弃生活”理念的兴起,中华文化中自古以来的节俭精神正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不过,相比制度约束更为重要的是在亿万心灵深处,培植起对每一粒稻米的珍惜,对每一滴汗水的礼赞,对至善至美的追崇,以使节俭成为一种文明的自觉。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