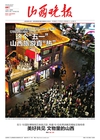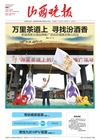张良仁:考古硬知识也充满烟火气
“宋人极为喜爱面食。花样百出的面制品也是城市中日常售卖的食物,人们常统称它们为‘饼’。北宋黄朝英的《靖康缃素杂记》云:‘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三者都相当流行。城中居民往往可以在‘坐贾’和穿梭在城中的‘行商’处买到面食……”这些文字出自考古学教授张良仁的新作《吃的中国史》,这是他两年探店的心血集锦,全书用丰富的故事、简明的史料,富有烟火气的笔触,让硬核知识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张良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伊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中俄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主要从事中国西北和外国西亚地区的考古,访问和挖掘过的国家加起来能绕地球一圈。在这个崇尚科技与快速变革的时代,即便是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人,也难免为历史文化的传承而焦虑。张良仁改进现状的尝试相当特别——2023年,他选择成为一名短视频博主,致力于以通俗生动的形式普及饮食文化知识。
从讲台上到镜头前的跨界并不容易,对此,张良仁早有预料。但他坚信“考古不是高冷孤僻的学科,历史不是尘封在书架上的知识”,他以美食为切入点,孜孜不倦地为观众讲述食物背后源远流长的历史。这份初心得到了回报,2024年2月到3月期间,他增长了130万粉丝,成为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的“招生代言人”。
经过两年的探店和拍摄,张良仁在全网积累的粉丝已经接近两百万,吃过和讲过的美食数不胜数,这些深入浅出的知识散落在不同的短视频中。时至今日,他的心血终于集结成书,定名为《吃的中国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自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讲起,收束于清代八大菜系的形成,全书有扎实的原始文献依据,如《晋书》《齐民要术》《世说新语》《宋书》《魏书》《洛阳珈蓝记》等;也有详细的考古现场解析,如奥海罗Ⅱ遗址、上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良渚古城、妇好墓、马王堆汉墓、曾侯乙墓、南海一号沉船等,再现了生生不息的饮食文化长卷,堪称一部吃的百科全书。
近日,张良仁教授举行新书分享会,并接受媒体群访,他说:“食物并非一家一户的小事,而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它的生产、加工、消费和流通,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们通过食物紧密联系起来,就像我们人体内的毛细血管一样,为社会输送了各种各样的营养。”
以博主的身份通俗地来讲考古
山西晚报:从考古学家到美食博主,如今回看这样的身份跨界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张良仁:严格意义上讲,我好像不够资格成为一个美食博主。第一,我不会做饭;第二,我吃包子也好,吃其它食物也好,要说这个东西怎么好吃、怎么做出来的,我也讲不清楚。我能讲讲这种食物、食材、烹饪技术是起源于什么年代的,怎么发展的,比如陶器怎么发展的,或者食材怎么演变来的,这是我擅长的东西,因为我在做考古。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跟我的同事讲,万物皆可考古。我们身边的各种东西,我们穿的衣服、帽子,坐的车子,都有历史渊源,食物更是如此,而且渊源尤其丰厚。
山西晚报:考古范畴也很广泛,您为什么选择了“美食”为切入点?
张良仁:1987年高考时,我的志愿是北大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系,由于分数不够被调剂到考古系。最初,深奥晦涩的考古课程让我“倍感头疼”,直到后来相继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阅历和学养不断加深,我才慢慢体会到这门学科的独特乐趣。在美国读博士时,我学的是俄罗斯考古,属于中国艺术史系。我还旁听了日本考古、希腊考古、秘鲁考古等课程、讲座,世界上好多地方的考古状况我都了解,眼界被打开了,我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也彻底改变了。
2019年回国时我就想做这样的事情:一是做外国考古项目,二是开外国考古课程,目的就是想打开中国公众的眼界,认识一下外国历史、文化的精彩,这是我的一个愿望。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碰到一些困难,尤其是这两年,一方面是我们的学校、老百姓,对这方面的事情不是那么理解,所以我想以博主的身份,通俗地来讲这个事情,这是我的一个初衷。也正是在考古领域的深耕,让我有了撰写美食史的想法。从2023年到现在将近两年,我积累了一些粉丝,非常感谢线上、线下朋友的抬举,我在线下也碰到好多粉丝,我认为他们非常了不起,非常感谢他们的喜欢。
山西晚报:做饮食的考古研究也是逐渐发展而来的,是吗?
张良仁:我这本小书的灵感就来自著名美籍华裔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他在相当早的年代就阐述了饮食与历史的紧密联系。自张光直先生以来,很多学者一直在长期研究饮食背后的文化历史,这其实牵扯到我们考古界、历史学界研究范式的转变。那个时候大家重点在关注文明起源、科技史这样的大话题,像什么研究饮食、研究筷子,都属于旁门左道。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整个社会都转变了,学术界也转变了,开始关注我们身边的事物,吃的、穿的、用的,这都被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开始关注老百姓关心的东西,总体来看研究多元化的趋势相当明显。
用“国际胃”发现中外饮食的不同
山西晚报:您在全球各地从事考古工作,在东亚等各种跨文明区域交流,应该吃过不少美食。
张良仁:这我可以吹点牛,因为我的经历还是比较丰富的。我老家在浙江,然后到北京上大学,在北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去美国留学。留学的时候因为研究俄罗斯考古,所以经常跑俄罗斯,归国以后跑伊朗、中亚、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也去过。所以我的胃,我称之为“国际胃”或者“世界胃”。无论在哪儿吃饭,都没有我吃不下的东西,通过这些经历我也发现中国饮食跟外国饮食很不一样,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就是中国人喜欢炒菜,这离不开宋代冶铁技术的成熟和铁锅的普及,我们熟知的菜谱也是随着“炒菜”的定型而诞生。此外,利用特殊的器皿“甑”蒸熟食物,也是中国先民的独到发明。而西方最常见的烹饪是“烤”,我曾在伊朗发现了距今5000年之前的青铜烤炉,我的学生在意大利发现了面包房遗址。但古代的中西饮食也有共同的地方,我去过奥地利的哈斯塔特,那里有一个盐矿,古人在那里采盐。矿场周围留下好多吃的东西,包括小麦、肉类、一些蔬菜,放在一起煮,跟我们古人吃得一模一样。
张光直先生最早从人类学的眼光来观察饮食问题,他讲中国饮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饭菜二元。中国人吃饭,光吃菜没有吃饭,觉得这顿饭没吃。但是中国人也绝对不会让光吃饭不吃菜,那也不礼貌,一顿饭也不完整。
山西晚报:我们的确是这样吃的,而且吃饭离不开炊具。我们逛博物馆就会发现很多青铜器都是炊具、厨具,看您的书也会知道原来在宋代的时候,铁锅才普遍开始应用,请您给讲讲炊具的历史吧。
张良仁:这就讲到冶金史了。人类最早用的炊具是陶器,当然他们可能还会用动物的皮作为厨具,更简单的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灌上水,把石头烧红丢到水里边,把水烧开煮东西吃,这个比较费劲。还有就是烧烤,把肉挂起来烤,也能用石板把饭烤熟。青铜是一种非常昂贵的金属,一般局限于社会上层使用,而且它不是在厨房里用的,是在宗庙里面用的。在商代、周代,甚至到汉代,祭祀祖先时,像鼎、鬶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摆在宗庙里面的。每逢重大节日祭祀时,就会让一个小朋友装扮成祖先,跑到宗庙的屋顶上去召唤祖先回来,到宗庙里享受后代供奉的肉、粮食,还有音乐。在古人的想象中,祖先会一边听着编钟,一边享受鼎里面的肉。青铜器大多是在墓葬里发现的,因为死后的世界也需要祭祀。
铁器一开始也是非常昂贵的东西,古代冶金技术比较落后,所以铁非常难得。铁器一开始更多的是用来做武器、农具,做炊具是宋代以后,因为宋代开始用煤炼铁,铁的产量一下子猛增。当时我们的铁还会出口,在南海一号沉船上面就有很多铁,是用来出口的。所以当时我们的铁在日本、东南亚都是非常畅销的。
借助短视频使文物带上生活温度
山西晚报:通过阅读《吃的中国史》,也会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祖先,在选择各自文明的基础粮食这一方面还是有些偏差的。
张良仁:老话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上长什么就吃什么,河里长什么就喝什么。所以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南方野水稻比较多,他们采集野稻子吃。北方就是野生粟比较多。先民还采集树上的果子、水里的鱼,有时候还刨草根来吃,有什么吃什么。我们最早驯化了水稻、粟、黍,还有猪、鸡这些动物。到后来小麦、大麦从异域传播过来,又有了羊和牛,便丰富了我们的食物,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土地的利用率。像粟、黍适合山地来种;水稻需要非常低平的平原;小麦需要灌溉,灌溉的话就也要找平地来种;像马铃薯、玉米、红薯这些农作物可以在水灌溉不到的山地种植。这样一下子就扩大了耕作面积,粮食也增加了,有时候干旱年份水稻歉收,玉米、红薯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荒年。
在漫长而多元的历史进程中,食物一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肉类熟食让成汤军队“无敌于天下”,周代列鼎制度标志着饮食礼制的高峰;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推动着茶叶官营制度的建立,宋元发达的海上贸易又让茶文化在西洋蔚然成风;大航海时代新大陆的作物传入中国:西南地区缺盐,人们就以辣椒代替食盐调味;番薯、玉米的引入又养育了明清繁盛的人口,清朝乾嘉年间人口就快速增长,从一点几亿到了四亿。
山西晚报:您在书里说河南贾湖发现骨笛的遗址,同时也发现了先民有酿造葡萄酒的习惯。在人们认知中,酿葡萄酒好像是西方的事,但九千多年前的贾湖就已经出现了?
张良仁:其实贾湖遗址的葡萄酒跟我们今天喝的葡萄酒不是一回事,它的葡萄酒是中国本土产的野葡萄,发酵以后形成的葡萄酒,大概还加了别的食物在里头。今天我们喝的葡萄酒是西方引进的葡萄,叫栽培葡萄。
人类喝酒的历史是很悠久的,远远不止九千年,应该还可以往前推。因为酒这个东西,只要从野外摘了水果,把它放一放,就会自己发酵变成酒,所以饮酒还可以往前推到旧石器时代,只不过这需要我们发现它,从考古学上证明它。我们要找到存留物,经过考古学上的化验,找到酒酸,证明它是酒就可以了,将来有可能会破掉这个“九千年”的记录。
山西晚报:说到“留存物”,您也正在用短视频这种形式留存,创造新的人文价值。
张良仁:用短视频记录生活的确也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保存方式。普通老百姓用手机随时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不仅满足了精神需求,也保存了海量的史料,使未来的历史学家有足够的资料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平凡人的美食、厨艺和烟火气。我在探店时,常常去路边摊、苍蝇店,目的就是记录平凡生活的历史。
在创作美食短视频的两年里,我到访过很多城市,也吃到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北京烤鸭、黄元米果、三杯鸡、大盘鸡、羊肉泡馍、骨酥鱼、烤肉……这些食物及其背后的历史,都蕴藏着一座城市变化发展的进程。借助短视频平台传播考古知识,能将专业性叙事转化为有美感的视觉体验,引起观者的情感共鸣,从而使文物带上生活的温度,让考古从学术象牙塔走进日常生活。通过短视频这一形式,我能将充满烟火气的中国史传达给更多的人。
山西晚报·山河+记者 白洁
《吃的中国史》书摘
宋代市井珍馐与饮食业的发达
两宋时期的蔬菜种植极为发达,在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不少志书和文集都记载了丰富的蔬菜物产,甚至出现了像《菌谱》和《笋谱》这样专门描述某类蔬菜的书籍。《淳熙三山志》著录的临安府的蔬菜有生菜、菠菜、黄瓜、冬瓜、江葫芦、山药、萝卜、茭白、菌、芹菜、芋头、韭菜、葱、姜、蒜、牛蒡等数十种。同时,宋人发展出了众多蔬菜的加工储藏办法。汴京夜市中常见有辣子姜、辣萝卜、咸菜、梅子姜等腌渍加工的蔬菜。
宋人喜食羊肉,但食用猪肉的规模不断增加。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城内的朱雀门外还有一条“杀猪巷”,该巷“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每天更有大量的猪通过皇宫对面的南薰门进入城中,满足大众的口舌之欲——“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十几个人赶着上万头猪,数量上或有夸张,也算得上一种奇景了。除羊肉、猪肉外,大城市还普遍出售鸡、鸭、鹅等家禽以及兔、鸽等野味,兼买卖生鱼、螃蟹、蛤蜊等水产。品类之盛,完全不亚于现代。
丰富的蔬果和肉类供应,是宋代城市美食得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汴京城内“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置饮食,不置家蔬”,大量都城市民都直接去店里买饭就食,“下馆子”的做法蔚然成风。人们对于就餐环境的追求也达到了新高度。大都市的“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高层楼阁,胜似园林,建筑别致、环境舒适。从小子亦即包间俯瞰下去,热闹的街景一览无余。同时,两宋时期人们在饮食时普遍使用椅子。在考古发现的两宋时期宴饮壁画,或者传世的绘画作品中,可见人们或站或坐,少有席地而坐的人了。
饮食业的高度发达,推动了服务业的蓬勃发展。酒店随时备有不同的菜品。一种是即来即食的“茶饭”。说是“茶饭”,实际上包括面食、羹汤、烤肉、肉串、炒菜、河鲜等多种食物。这些“茶饭”必须满足随叫随到、随时齐备,是平时生意的基本盘。客人只需叫店小二来——当时的服务员实际上叫“小儿子”,民间戏称“大伯”——报上自己要点的菜,就能够享受“即时供应”的菜肴。
“外来托卖”,这种穿梭在大街小巷、托着餐盒与盘子叫卖的流动摊贩也很普遍,《东京梦华录》记载的托卖餐品有不少热食。或许街边店家刚做好这些菜,就有人拿出去叫卖;他们盛装热菜的餐盒还有保温功能。托卖菜品中还有大量的干果、水果与蜜饯,相对来说它们可以保存得久一点。托卖菜品的食品卫生也值得信赖。杭州的摊贩“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耀人耳目”,正是“学汴京气象”。在南方城市的河道中,人们还会撑船买卖菜肴,提供茶酒,发展出了提供饮食、小吃、娱乐、钓鱼、冬日观雪等不同服务的船只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