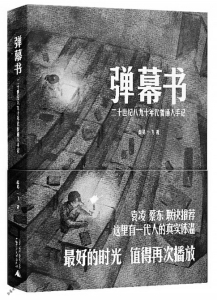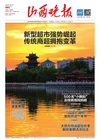1位叙述者与50位读者的纸上对话,《弹幕书》节选——
1989:麦收如火
《弹幕书》
薛易 一飞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学年为标志,回忆了一个80后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苦乐交加的成长经历。1984-2003年不仅是作者成长的20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发生巨大变化的20年,通过作者的回顾,我们可以重温那过往。书中除了作为主要叙述者的作者,还有一个由50位读者组成的“时光点评团”。弹幕形式的点评、对话,让整本书不再是一个人的记忆,而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故事。
那时,我们周围的学校没有寒暑假。一年有三个假期,分别是:麦假一周,秋假三周,年假三周。
麦假和秋假是农忙假,小学生要帮家里干活。年假,顾名思义,就是过年了。
农忙假不是“过家家”,小学生是真要干农活的,尤其是春夏之交收麦子的时候。俗话说,“一麦赶三秋,官家小姐下绣楼”,说的就是麦收时节,农活铺天盖地而来,要没日没夜地忙,任你再怎么娇贵,都得下地干活的。
麦地之美,无数作家和诗人曾赞美过,在农民心中,更承载着全家人一整年的生活和希望。每一个麦穗都沉甸甸的,每一根麦芒都直刺青天。烈日高悬,催促着抢收,快些、再快些。
麦子是自家的,没人敢抢你的,为什么还要抢?又抢些什么呢?
其一,抢时间。麦子由青变黄,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麦子跟玉米不同。玉米熟了,即便不从秆上掰下来,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但麦子熟了,如果不及时收割脱粒,就会从麦穗上炸飞,散落到地里,再也收不起来。那种减产将是致命的。
其二,抢天气。麦收时间本来就短,又值暮春初夏,时常下雨。一旦碰上阴雨连绵天气,麦子就可能收不回来了,即便收回来也只能堆在场院里等天晴。若不及时晾晒,麦子就会发霉,甚至发芽,一年心血付诸东流。
其三,抢场院。麦子收回来,要在场院里摊成薄薄的一层,暴晒一两天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村里的场院面积有限,分给各家也是不大的一块。然而,每家少则七八亩,多则十几亩地的麦子,自家场院根本不够用。只能跟邻居协调好时间,轮番晒麦子,一般都是谁先收谁先晒。
所以,抢字当头,麦收如火。
麦地变黄了,扒开麦穗,看看麦粒饱满了。父亲连夜把镰刀磨得雪亮,看哪个镰头松了,就垫上一块破布,务求锋利、称手、结实。我也分到一把短柄镰刀。之前早有了割草的经验,父亲只是叮嘱我,握镰刀的手一定要稳,离腿要远一点,免得被割伤了。
我心里有点儿期待,有种电视剧里大战前夜的感觉。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家里只剩下奶奶,父母早就下地去了。每到农忙时,奶奶都从城里回来,帮着做饭以及照看我。我有点生气,为什么不等我?“你别着急,他们过会儿就回来吃饭了,吃完饭你再跟着去。”奶奶一边说着,一边把和好的玉米面倒进热气腾腾的大锅里。
其实,所谓“丰收的喜悦”,那是在收割之前和完事之后才会有的,在割麦子的过程中,心里除了“割”之外一无所有。割麦子要一手把住麦穗下面的位置,一手用镰刀朝麦子根部用力割,两只手都要握紧,若是滑脱了要么割伤手、要么割伤腿。麦子看着金黄,但真要割起来,走不出十步,手就会变得乌黑。割得久了,脸上,连同鼻孔里也是黑的。骄阳似火,汗水滑过眼皮,噼里啪啦落在麦子上。大人们个个如临大敌,弯着腰全神贯注地收割,小孩很快就被甩在后面。心里着急也没用,只能小心再小心,免得受伤,帮不了忙还添乱。
后来,我曾多次跟出身农村的朋友聊起童年割麦子时的感受,发现大家都常用同一个词:绝望。那感觉真是绝望。麦垄几百米长,弯腰久了,抬头一看,两眼发晕,一步步挪过去,好容易到头了,接着就要再折回来。有位朋友明确表示,他就是在割麦子的时候下定决心一定要“考出去”,绝不想再干农活了。
我的手上很快就起了泡,一使劲就疼,速度变得更慢。父亲在我前面大喊:“别割了,你回家去拿点儿水吧!”我如蒙大赦,掉头就往家走。
割完了麦子,要用牛车拉到村头的场院去,这时最适合我干的活来了。熟透了的麦子很轻,牛车上每次都装得满满的,足有两三米高,需要有人趴在车顶的麦子上,帮车下的人用绳子拢好。这个活叫作“压车”,一般都是小孩干,因为小孩足以胜任,身体也轻,不会给牛增加太多负担。不过,压车并非毫无风险,身处高高的车上,地下都是刚割完的麦茬,断口尖锐。一旦拉车的牛受惊,或自己不慎掉下来,很容易被刺伤。
当然,相比于秋天的玉米茬,麦茬要“温柔”多了,玉米茬断口才真是锋利如刀,一旦落到上面,立刻就会被戳个窟窿,血溅当场。
但我还是喜欢压车,趴在车顶不用走路回去。那种居高临下又晃晃悠悠的感觉,让我有一点儿陶醉。有时还伸出手,掰几根伸到面前的柳枝,结一个柳环,戴在头上,很风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