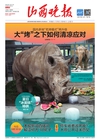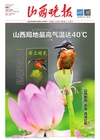大树底下好读书
老槐树荫下的阳光是筛过的。七月的烈日穿过层层叠叠的叶片,落到青石板上时,只剩些碎金似的光斑,像谁不经意撒了一把铜钱。我总爱把竹椅搬到树荫最密处,椅脚压住几片早落的槐叶,发出细微的脆响。蝉在头顶嘶鸣,却奇怪地不让人觉得吵闹,倒像是给寂静做的衬底——在这般光景里翻书,连纸页摩挲声都格外清晰。
这槐树是祖父年轻时栽的,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树皮沟壑纵横,我常把脸贴上去,嗅那股子带着苔藓味的凉意。树根隆起处形成天然的矮凳,祖父生前最爱坐在那儿抽旱烟。烟锅里的火光一明一灭,青烟袅袅上升,与槐花的香气混在一处,竟分不清哪缕是烟,哪缕是香。如今树根凳空了,我却总错觉那烟味还悬在空气里,混着书页的油墨香,成了夏日独有的气息。
我看的书杂,从《水浒传》到《十万个为什么》,统统堆在树下的藤箱里。书脊被晒得褪了色,书页边缘卷曲如浪,有几本还留着雨渍晕开的痕迹——那是去年夏天暴雨突至,我抢救不及留下的印记。母亲见了总要唠叨,说书该放在干燥处,我却觉得带着水痕的书页翻起来更有滋味,仿佛字里行间藏着雨声。
正午最热时,树荫会悄悄挪位。我跟着阴凉调整竹椅的位置,像向日葵追着太阳转。有回读《西游记》入了迷,没察觉阳光已爬上脚背,等脚踝火辣辣地疼起来,才发现凉鞋带已在皮肤上烙出两道红痕。母亲从灶屋出来看见,也不说话,只递来一碗冰镇的绿豆汤,碗底沉着两粒饱满的葡萄干。
树上的居民们对我这个常客早已习以为常。蚂蚁队伍绕过我的凉鞋,在椅腿处兵分两路;花大姐偶尔停驻书页,翅膀收拢时像枚别致的书签;最胆大的是那只松鼠,常蹲在矮枝上啃果子,渣子簌簌落在我肩头,像下了一阵温柔的雹子。有次它竟顺着我裤腿爬上来,小爪子搭在《昆虫记》的彩页上,黑豆似的眼睛盯着图画里的甲虫,须毛轻颤,仿佛真在思考法布尔的论述。
读书倦了,我便仰头看树叶间的光斑。千万片槐叶在风里翻飞,背面的银白与正面的翠绿交替闪现,整棵树成了巨大的万花筒。看得久了,眼前会浮现奇异的幻觉——那些光斑化作书里的字句,在视网膜上跳舞:“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睡意袭来时,书往往滑落在地,惊起几只正在文字间觅食的蚂蚁。
某个夏日午后,我在藤箱底层翻出本陌生的旧书。牛皮纸包着书皮,扉页上是祖父工整的毛笔字:“1965年夏于槐荫下读”。书页间夹着张发黄的照片:年轻的祖父坐在树根凳上,膝头摊开的正是这本《唐诗三百首》,身旁站着穿碎花裙的祖母,手搭在他肩头。照片背面写着:“是日小满,槐花初放。”我摩挲着照片,突然嗅到一缕若有若无的槐花香——原来那页正好是王维的《辛夷坞》,“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诗行间,还粘着半粒干瘪的花蕊。
黄昏的阅读最为珍贵。西晒的阳光变得柔和,把书页染成蜜色。蚊虫尚未出动,晚风先送来了井水泼洒院子的清凉气息。母亲这时常来树下纳鞋底,针线穿过千层布的声音,与我的翻书声一轻一重,竟成了奇妙的二重奏。她偶尔问我书中故事,我便把“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讲成“贾家小姐们比赛写春联”,将“拳打镇关西”说成“鲁达教训恶霸”。母亲听得入神,针脚便乱了分寸,在鞋底上留下歪扭的轨迹。
如今老槐树依然亭亭如盖,只是树下少了纳鞋底的身影,多了个捧着平板电脑的侄儿。他嫌树荫里信号弱,总想回屋连WiFi。我强行塞给他一本《西游记》,他翻了两页就嚷字太小。直到有只蝴蝶停驻书页,翅膀轻轻开合,鳞粉在阳光下闪着微光,他才安静下来,小心翼翼地伸出食指……
蝉声忽然大作。我合上膝头的旧书,发现树根凳上落了几朵早开的槐花。拾起一朵夹进书里,忽然明白祖父当年为何独爱在此读书——树荫会移动,书页会发黄,唯有翻动纸张时带起的微风,与头顶永恒的沙沙叶响,才是岁月最忠实的读者。它们年复一年地阅读着树下的故事:一个捧书的孩童如何长大,又如何老去,而槐花年复一年,落在不同代人的肩头,像一个个温柔的句读,标记着时光的诗行。
□林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