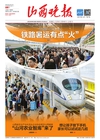以诚为本
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承载着诚信、诚实、诚朴等丰富内涵,代表着真实无妄、表里如一的崇高品格。从儒家经典到历代家训,“诚”始终被视为立身之本、处世之基。孔子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则强调“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这种对“诚”的推崇构筑起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
孝亲贵在诚。朱熹有言:“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宋代龚明之为人至诚至孝,是名闻朝野的道德楷模,他在家训中称“吾一生受用,只一‘诚’字”。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深刻指出“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真正的孝道不在于表面的礼节周全,而在于发自内心的诚挚与笃实,即使没有繁琐的形式,只要怀有至诚的孝心,同样能感天动地。孝的真谛在于“诚”,若能以真诚之心体察父母所需,即便一句温言、一次倾听,也远胜于虚浮的排场。这种根植于诚笃的孝行,才是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精髓所在。
为学贵在诚。孔子教导子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揭示了为学的基本态度。读书一事,看似寻常,实则关乎心术。清代陈宏谋在《养正遗规》中谆谆告诫子弟:“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这种严谨的治学要求,本质上是对“诚”的践行。林良铨在《麟山林氏家训》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读书须用自己实在工夫,若粉饰欺人,便是自欺,自欺则无诚意,学问那复有长进处?”这种态度不仅关乎知识的获取,更是人格养成的关键。因为学问之道,即是做人之道。
交友贵在诚。孔子云“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朱熹也提醒后人“交朋友,贵乎信也”。清代李淦在《燕翼篇》中直言:“信为交友根本。”窦克勤在《寻乐堂家规》中提出了“信”的标准,“朋友贵乎信,一与之言,心口如一;一与之行,内外不二,方为君子之交”。王士俊《闲家编》也强调“非交不成其为友,非信不成其为交”。管仲与鲍叔牙的“管鲍之交”,范式与张劭的“鸡黍之约”,都是诚信交友的典范。倘若表面诚恳,内藏机心,言辞恳切却心怀诡诈,则不过是小人之交。“诚”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经营贵在诚。明清时期晋商、徽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即信义为先,利润为次,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清代陆一亭在《家庭讲话》中指出:“交易须要公平,不可说骗欺人。斗秤须要一样,不可轻出重入。”“凡相与交易者,须要两不伤亏,方称公道。”这种商业伦理在各类商业典籍中也有系统的阐述。历史上,胡雪岩书有“戒欺”二字的匾额高悬堂上,乔致庸把“信义利”三字作为家训,都体现了诚信经营的价值。
治国贵在诚。清代张履祥在《训子语》中说:“天地间人各一心,心有万殊,何能疑二不生,始终若一?所仗忠信而已。以忠信为心,出言行事,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久而家庭信之,乡国渐信之,甚至蛮貊且敬服之。”曾国藩在《复贺耦庚中丞》中也总结道:“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回顾历史,商鞅在变法之前“徙木立信”,让秦国百姓知晓政令之重、官府之信,从而奠定了变法基础。诸葛亮“七擒七纵”,以真诚之心让孟获折服,确保了边疆的长期稳定。在当代社会治理中,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国际交往中的信誉的积累,无不延续着“诚”的传统智慧。
从个人修养到国家治理,“诚”贯穿中华文明的各个层面。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重拾“诚”的精神内涵尤为重要。正如《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诚”不仅是过去的道德准则,更是面向未来的文明智慧。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