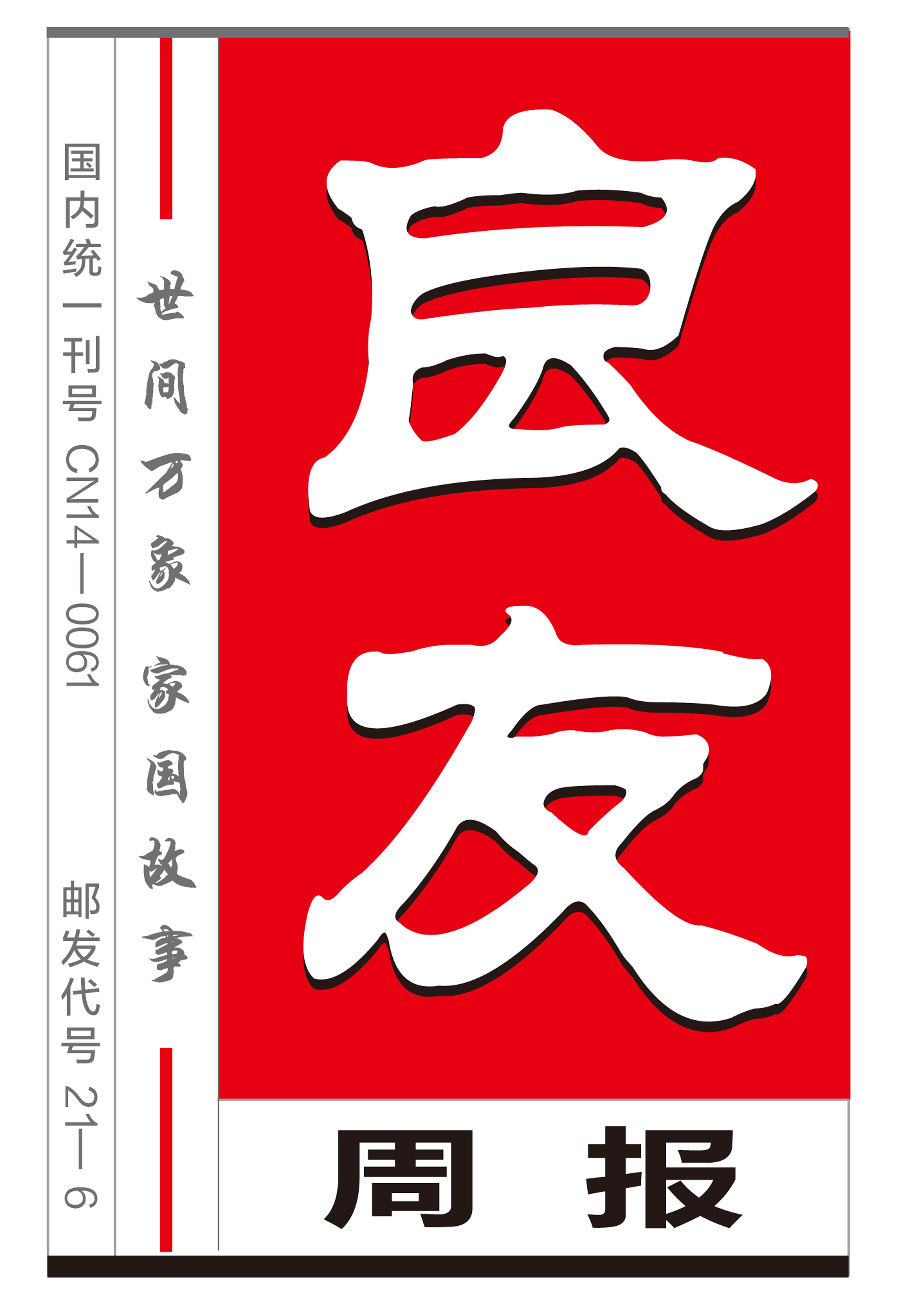【故纸堆里寻安全】肆:武王伐纣,权把鸩酒对君酌
面对武王的军事征伐,商纣王采取的自卫反击行动,可以看做是典型的救援失败案例。
周武王十二年,公元前1044年,二月甲子日的凌晨,面对武王姬发的突然袭击,仓促间,商纣王紧急征调了京城周边奴隶和监狱中的犯人七十万人,组成临时军队仓促迎战。
从人数上,商朝的军队占有绝对的优势。武王仅率领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戎装将士四万五千人。对于崇尚武力又天生睿智的纣王来说,武王的行为算是以卵击石。
按照史书上的记载,纣王至少有三项过人之处:天生力大无穷,可以徒手与野兽搏斗;天赋聪颖,口才卓越,有很强的煽动性;有超强的国家统治能力,在经济建设中又有他独到的思维和方式。
明代许仲琳的志怪小说《封神演义》中,在纣王的社稷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纣王身边依然有闻仲、箕子、费仲等能臣干吏的存在。即便是在武王起兵的关键时刻,瞬间能将七十万人组编为一支军队,可见纣王在组织能力、统筹能力和应变能力等方面,有着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社会统筹能力。
纵观先秦历史,夏桀和商纣有很多相近和共同之处,如为政不修、贪图安逸以及牝鸡司晨等。中国历来有红颜祸水的说法,以夏桀的妹喜、商纣的妲己为代表,反向来举证亡国之君昏庸好色的本质。
传说本身就是演义。无论是夏桀还是商纣王,都有着无比的自信。夏桀用太阳来比作自己,只有太阳消亡了,他才会消亡。而纣王更是不相信命运的人。西伯戡黎后,大臣祖伊惊慌失措地向纣王报告,说黎国作为商朝龙兴之地,现今已经被周国灭掉,这是上天的惩罚,也是断绝了商朝的气运。纣王则毫不介意,他说,命不在天,又何必担忧。
反观周武王所带领的西岐军队,尽管踌躇满志,但也没有攻必果、战必胜的信心。甚至在武王姬发率领大军渡过盟津的时候,还祈求上天将胜利的天平倾向大周。在武王的内心世界里,早已做好了失败的打算: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武王姬发之所以敢率军攻打商纣王,是因为他有着最起码的防御底线,即失败后可以退守西岐,凭借黄河和潼关天险保住自己的封地。作为国家战略防御的高级体现形式,以攻为守或者试探性攻击或许是武王的上佳选择。
历史几乎是重演。在商汤灭夏时,重臣伊尹也采取过相同手法。商王用了近二十年时间,采取分化瓦解的方式,将夏桀京畿周边的小国据为己有,对夏桀形成了战略性包围。商汤对最后决战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几经试探和权衡方才作出决定。立国近400年的夏王朝,即便已面临灭亡之时,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当商汤在伊尹的建议下停止向夏桀纳贡以试探其反应时,夏桀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视情况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贡职”,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传来了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商汤乃再行停止向夏桀的贡奉。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了,九夷之师不起,有诸侯公开反抗。此时商汤见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才下令起兵征伐。
在商纣和夏桀的战略防御体系中,首先是错误地将国家安全保障放在邻国间联合抗敌和盟约的基础上。这样的做法,尽管在联盟初期可以有效地拉大战略防御纵深,但由于联盟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极其不稳定,随着条件变化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盟国的倒戈会瞬间造成战略纵深的消失,遥不可及、看似无关的危险源会瞬间来临。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武王伐纣最终形势出乎所有人预料,一夜之间七十万军队完全倒戈,瞬间就让商王朝土崩瓦解,纣王以鹿台自杀的悲剧完成了他作为“英雄”的最后展示。
传统认为,“小邦周”通过著名的牧野之战能一战而胜“大邑商”绝非偶然。周武王争取人心、翦商羽翼、乘虚进攻的谋略与商纣王缺乏警惕、毫无防范、多面作战形成了鲜明对比。
“祸生肘腋”这个中国历史上耳熟能详的成语,事实上昭示着危险源的产生通常不是以“很暴力、很恐怖”的形式出现,更多的则是不经意甚至是主观上认为“不可能”或者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发生。武王和商王的每一次军事行动和外交行为,都是对纣王和夏桀的风险累积,当量变到质变的时候,便是改朝易代的时候,也将开始对前者心理和生理最大的折磨。
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在迷信鬼神的时代,打破了君王永固的思想。除去历史和政治意义,两件征伐事件本身还为现代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带来巨大反思。
西汉刘向《说苑·敬慎》篇有云:怨生于不报,祸生于多福,安危存于自处,不困在于蚤豫。就是指祸生于安享的太平,太平的骄奢淫逸定会成为灾祸的本源,麻痹大意瞬间就是危险源的出现。
更为恐怖的是,当将危险源错误地判断为安全信号时,面临的必将是灭顶之灾。商纣王的错误就是在毫无应急预案和无兵源可用的情况下,强行将政权专制对象奴隶与罪犯配发武器哄上战场,成为他失败的直接原因。
现代应急管理是指相关机构在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善后恢复过程中,通过建立必要的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应用科学、技术、规划与管理等手段,来保障安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前提只要有一项关注,失望的结局将不会发生。
纣王在缺失了制度保障、物资保障的前提下,没有采取任何有效防范措施。在饮鸩止渴般的奴隶上场倒戈后,直接造成了他的心里崩溃。用一个不确定因素去影响甚至希望更改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主观上的形而上学,并不能对任何一方产生本质影响,因此纣王之死也成为必然。如同要抢救一名落水者,偏偏却扔给他一块秤砣。
事实上,纣王还有另一种选择:逃离。从单纯生命的意义讲,纣王可以选择逃离他的驻地京师朝歌,图谋东山再起,也不失为上策。但是毫无思想准备的纣王不假思索就结束生命,显得过于草率,暴露出他心里承受能力此时已经完全崩溃。
在现代救援案例中,被救者本人的心理素质在漫长的施救过程中将起到关键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不可抗力等突发事件来临时,被困者的镇定自若或许将会迎来最佳救援时机。
或许,这是商纣和西岐战争故事给现代应急理念的又一点启发。
王清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