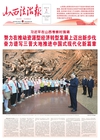亲情破冰记
车轮碾过被雨水泡得发亮的盘山路,窗外是连成片的青灰屋檐和湿漉漉的农田,小麦已经收割,播种下不久的玉米才刚冒头,这抹葱郁的绿让通往泽州县人民法院川底人民法庭的路途变得格外亲切和温暖……
调解室里的剑拔弩张
刚刚踏入法庭就听到了激烈的争吵声,“那房子当年本就是分给我的,怎么一转眼就成了你们老大家的了?笑话!那房子砖瓦木料都是我的!”六十岁的老张声音嘶哑。
另一边,年纪稍大些的刘大妈也毫不示弱:“账不是这么算的!你不能昧着良心说话,这房子后来翻修、伺候老人,这些年的付出你们老二家参与过一分?补偿款下来了你就想回来一口吞?哪有那么好的事!”坐在刘大妈旁的小张听了母亲的话,更是脸绷得紧紧的,脖子上的青筋微微跳动。
调解比约定时间开始的更早,循声步入调解室,川底法庭的庭长陈海波与案涉房屋所在村的村支书坐在中间,书记员在旁记录,两边是剑拔弩张的叔侄两方。
陈海波没有立刻介入这场火药味十足的“控诉”,他目光轮流落在双方当事人脸上,手中拿着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相关证据以及案涉相关材料,在倾听双方委屈和不甘的过程中无声地提取着与案件紧密相关的事实,并在笔记本上不时写写画画,梳理着案情、诉求及相关疑点。
“都冷静一点,好好说”“既然到这了,肯定是要给你们解决清楚的,先把事实说清”……
看着双方当事人情绪越来越激烈,陈海波出言安抚,并询问案件细节:房屋建于何时?近些年由谁居住维护?翻修过几次?补偿款何时发放?有无相关文件……临近午饭时间,案情越来越清晰,但双方的僵持却没有松动。调解无果而终,当事人前后脚离开法庭,陈海波与书记员也合上笔记本,收拾案件材料返回办公室。
谈及调解的失败,陈海波却很平静:“当事人既然来到法庭,说明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先得让他把肚子里的苦水或者怨气发泄出来……”
会议室里的集思广益
推开法庭里的小会议室,陈海波与法官助理、书记员正围坐在桌前。陈海波架起眼镜,指着摊开的村宅地形图,声音沉稳,“早上我们听了双方当事人的诉争,事情基本也捋清楚了,对于案件的处理,你们有什么想法?”
“原告老张坚持认为,老宅主体是其父母出资出力所建,他作为继承人理应多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属于遗产继承,那就应该考虑双方当事人是否尽到赡养义务……”法官助理卫舒宇思维敏捷,直接从法律关系切中痛点。
“被告小张强调他父母后期翻修投入巨大,且多年居住在里面对房子和老人的贡献更大,从情理这个角度我们也应该作一定考虑。”书记员原媛翻着笔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双方对老宅哪部分是后期翻修,以及房子所有权归属的说法差异很大,缺乏直接书面证据。这就是关键点之一。”陈海波用笔在图纸上圈出关键区域,指出,“坐在办公室里,永远听不到最真实的声音,看不到最关键的细节,必须找到能相互印证的客观事实或旁证。”他带着团队仔细梳理案件中需要核查的重点问题:实地查看老宅现状;找老邻居、老村干部,了解老宅建造和后续翻修的具体参与人员;查清赡养义务的具体履行情况;到叔侄家中进行走访,侧面了解双方的经济状况和真实诉求……会议室里,没有慷慨激昂的陈词,只有冷静的分析、务实的分工。通过复盘,接下来工作的目标已清晰。
川底法庭和大多数基层法庭一样,时刻被案多人少的问题所困扰。根据本周的排庭安排,这周只有这天及周五下午没有开庭,所以走访必须在下午完成。复盘结束,大家匆匆赶着最后的饭点就餐,短暂休息整顿便又马不停蹄出发。
用脚步丈量的真相
六月的雨毫无预兆,说下就下,眼前的晴空没过多久又变成了阴雨天。雨来得急促,陈海波带着法官助理、书记员和法警,一行四人踏着泥泞的乡间小路,直奔老宅所在地。
因为是危房,老宅早已废弃,站在斑驳的院墙前只能依稀辨出三间房的轮廓。陈庭长驻足细看,并向村干部核实搬迁情况及补偿细节。
很快三三两两的村民前来围观,幸运的是,正好碰到了老宅的旧邻居王大娘。法官跟着王大娘回到家里,坐在农家小板凳上,陈海波用带着乡音的俚语,先与王大娘拉家常,接着又问起了与案件有关的一些细节,“你是老住户了,还记得当初那房是几间吗?后面是谁张罗重砌的?”在飘着炊烟的院落、湿润的田埂边,在老人的回忆里,在老宅每一处痕迹的印证下,那个被争执模糊了的家族往事和房产归属的真相,一点点清晰起来。
心里有数,调解起来也能更有的放矢。陈海波又先后来到原、被告家中,用背对背调解的方式开始第二次的调解。
在被告家中,小张母亲刘大妈提及往事,情绪仍有些激动,小张也坦言:“叔叔在父亲在世时没有对老房提出异议,反倒是意外获得补偿款后产生嫌隙,一家人为了钱闹得不可开交,实在并非所愿。”同时,小张还提出自己一家长期居住并修缮房屋,并办理了确权登记。得知这一关键信息,陈海波立刻告知其应当向法庭提交证据,并提醒被告:“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会去核实,但是有关键证据你们也要及时提交,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法官办案不可能预先知道或了解案件事实的全部,因此要依靠证据来查明事实,即使你们自己觉得有一百个道理,但是如果没有证据支撑或者证据不够充分,证明力不够,那就不占理。”
在原告家中,老张提起往事时眼圈也不禁微微泛红:“陈庭长,不是我们争,是因为父母走得早,那三间房是我最后的念想,我好心让给大哥一家住,大哥去世了,大嫂在里面住我也没有说过一次要收回,结果有补偿款了他们一声不吭……我小孙子如今有病,医药费开销大,如果不是因为凑不够医药费,我也不愿意去要这补偿款。”
闻言,陈海波没有立刻回应,而是静静听着,待老张情绪稍缓,他才从法律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益以及人情的角度,表明法庭充分理解他对老宅的感情,明白他的困境,但在法律上也要考量侄子一家实际的付出。“咱们争取的,不是把对方压下去,而是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把情况摆清楚,把难处说明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一番话,没有空洞的安慰,而是清晰划出了法理人情的框架,老张听完,情绪平稳了一些,沉默点了点头。
多轮调和破僵局
带着走访得来的“拼图”,第二天早上八点,赶在另一起案件开庭前,陈海波再次将双方请进了“和事佬”调解室。包括陈海波在内,所有人都对这次调解信心满满,事实明了、证据链更完整、在背对背调解的基础上,双方态度也有所松动。再次坐在一起,也没有了第一次的针锋相对,甚至一言不合就吵起来的紧张氛围。
陈海波第三次主持调解工作,先摆事实,再讲法律,更讲情理,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分析利害关系,引导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理解对方难处。不料,叔侄的心结太深,一方觉得对方贪得无厌,另一方觉得长辈处事不公。经过几轮争执,调解竟然又一次陷入僵局,双方不欢而散。
没想到第二天中午,小张经过一天的考虑,主动联系法庭,称想与叔叔和解。趁热打铁,最后一次调解定在下午三点开始。
调解室里经过数轮法、理、情的交融疏导,再加上小张的态度松动,一个多小时后,调解方案一条条明晰并最终敲定。书记员赵宁宁立刻去制作调解协议书。在仔细审阅条款后,双方对调解结果进行了确认。
为了避免后续执行纠纷,法庭积极适用“立审执一体化”机制。根据调解协议,小张当场将补偿款向叔叔履行完毕,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调解室内,墙上的“和”字牌匾在无声见证,“握个手吧”,陈海波打破沉默。老张伸出手,握上了侄子的手。
“这多好,以后还是一家人!”望着叔侄紧握的双手,陈海波欣慰地说道。
谁能想到,生活中常被大家调侃“三棍子打不出一句话”的陈海波庭长,偏在最费嘴皮子的调解工作上常拿“满分”。入职20多年,他受理案件3121件,成功调解案件1910件,调解、撤诉率达六成以上。
当问及调解工作的诀窍时,他笑着说,“没甚,就是你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有颗正义的心。”这何尝不是万千基层法官的真实缩影?他们只为用法理的天平一头挑起人心分量,一头安放尘世安宁。
本报记者郭志平 通讯员李泽晴/文 张浩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