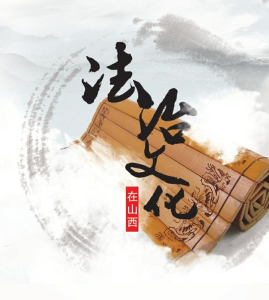于成龙判牍选介(上)
于成龙在清顺治18年(公元1661年),上任广西柳州罗城县令。此任6年中审理了一批刑事和民事案件,留下经典案例,在这些案件的判词中体现出于公秉持天理、国法、良心的裁判理念和宽严相济的裁判艺术,特别是他殚精竭虑的社会治理成就,受到当地民众的好评,同时也被清王朝政府举为“卓异”。
民国初年曾经出版发行了由虞山襟霞阁主编纂,衡阳秋痕廔主加评的《于成龙判牍》。笔者从中选择5件案例,作了简要的释评,以便于我们当代司法工作者借鉴。
(一)解除不法婚姻案
在司法实践中,某种行为牵涉刑事和民事交叉的案件古来有之,一般都采取同案同审、分别裁判的审理方式。于公在初任罗城县令时,遇冯婉姑刺伤吕豹变到县衙自首,并提出解除吕家婚约的诉求,吕豹变一方也同时状告婉姑行凶伤人。
依据本案事实,于公作出判决,肯定婉姑自首成立。民事部分的判决,对于婉姑第一次婚约予以肯定,“仍宜复尔前盟,偿尔素愿,愿你们花烛之夜,永结百年好合”,这就解除了被其父与吕家订下的强迫婚约。刑事部分的判决指出:冯汝宽(婉姑父)贪富嫌贫,弃良即丑,将漂亮的亲生女儿作为“奇货”,这是国法不容的事情,本应当惩究,念其痛哭悔过,暂且免了杖笞。吕豹变属于刁滑的纨绔子弟,以不法手段伤害了冯家父女之情,破坏了婉姑前约的婚姻,罪过不可赦免,应予杖责,以使这种冥顽人受到教育。
从此案的审理中看出:对刑民交叉的案件,在古代司法实践中采取同审异判的审判方式。于公在判词中支持良善,褒扬守法;针砭凶顽,鞭笞违法,作了充分的说理,具有借鉴价值。
(二)债务人赖债不还反诬告陷害债权人案
一个债权人因讨债未果,将债务人加以羞辱;债务人在气愤之下,状告债权人图谋造反。于公将两案进行了合并审理。经审理查明:本县县民吕思义祖父吕莘耕,曾向同乡陈敏生的祖父陈景山借过80千钱(即80吊铜钱)。后来吕家在本朝有军功,逐步发迹。陈家祖上在前朝(明朝)有军功,曾经兴旺发达,家资超过百万,但到儿孙辈家道衰落,陷入贫困,陈敏生便到吕家讨债。因吕思义不承认此事,被陈敏生羞辱一番。吕家气愤不过,欲以陈家祖上为前朝军人,今又勾结江湖亡命之徒图谋造反为由告到县衙。陈家知道此事之后,抢先把吕家拒不还债之事告到县衙。
于公作出的判决内容较长,分解为两项:1.陈敏生状告吕思义祖父向陈家借80千钱情况属实,有祖上借据为证。吕思义认为明朝的借贷关系进入清朝之后,自应灭失,属于认识错误。清顺治11年(公元1654年),福建省按察使曾因同类问题,向刑部请示前朝私人之间的债务如何处理。刑部回文称,前朝所有私人之间一切纠缠不清的事务,仍应以原来的律例判决,不因发生于前朝而销案,致使平民受损。据此认定,吕思义应当偿还欠款无疑。2.吕思义状告陈敏生勾结江湖亡命之徒图谋造反,纯属诬陷。陈敏生的父亲陈应龙是明朝桂林都尉,是明代臣子,抗拒清军是臣子的职责。大清统一后,顺治9年(公元1652年)曾有谕旨奖励抚恤明代殉国的臣子。吕思义怎么能以此为由诬告陈敏生?陈敏生虽当过明朝军人,但在大清一统之后,陈敏生回乡务农已有7年。本县3次搜查陈的住房,5次向陈的邻居调查,都没有谋反证据。因此,吕思义构成诬告罪,其目的在于赖债不还,用心阴险,令人愤怒。于公在判词的末尾,并历数世事的兴亡盛衰,以历史教育人们扬善弃恶。
判决:按照律例,诬告他人叛逆的,当以叛逆治罪,因念吕家率先归顺大清,在两粤地区作战多年,特予宽大,免其死罪,杖责二百,流放三千里,妻子和子女判充军,财资没收入国库,由官府从中拨出80千钱归还陈敏生。
判文后另书:制作详文向上峰按察使报送。此案判词精彩,准确引据律条,是相当完整的一个案例。赖债入罪古来有之,诬告反坐,处罚似重,律例规定如此。
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
《山西法治报》社宣
王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