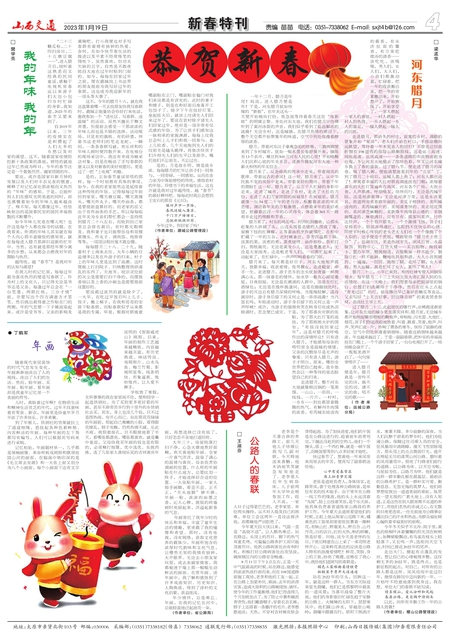我的年味我的年
樊学亮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磨豆腐……”,进入腊月后,闻听着这熟悉而又经典的民间童谣,感触于电视机里春运以来游子们大包小包归乡时忙碌的身影,我知道,2023年的春节又要来到了。
自2019年以来,三年的疫情实在是积攒起了人们太多的乡愁以及对家的渴望。这不,随着国家疫情防控新十条政策的落地,曾经的就地过年已然成为昨日,今年的春节注定是一个轰轰烈烈、阖家团圆的年。
要说,或许是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丰衣足食的惬意,稀释了对记忆深处那浓郁而又热烈的“年味”的感知。于是,总能听到人们在感叹光阴易逝的同时,却也感慨着如今的年味儿越来越淡了。殊不知,每天都像过年,恰恰映射出的是国泰民安的国民幸福指数的不断攀升。
如今年味儿究竟在哪儿呢?也许这是每个人都在探寻的话题。在我看来,所谓的年味儿其实就在每个人内心那丰盈愉悦的感知里,就在每每进入腊月那辞旧迎新的忙年中。当然,还有就是那经年聚少离多的乡愁,从来都会点燃我对年的期盼与热烈。
越传统,越“春节”!是我对年的认知与渴望!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每每过年最为喜庆热烈的便是写春联了。作为村上的文化人,只记得无论是爷爷还是父亲,每逢过年总会在“一台笔墨,两联红纸,三分才情”前,非要写出个四方满意方才罢笔。然后挑出最得意之作贴在门的两侧,年的气息便一下子被渲染起来。或许是受爷爷、父亲的影响及熏陶吧,打小我便也对手写春联有着情有独钟的热爱。奈何,在如今快节奏生活的推进以及平素不经常练笔的惰性下,虽然喜欢,但功夫欠缺的丑字,自然是不敢夜郎自大地在过年时贴到门前的。如今,每每在回家过年之前,便在潞城找上书法界的朋友提前为我写好过年的春联,这也成为我迎新年的一项头等大事了。
这不,今年的腊月十六,就在我还盘算着哪一天去找朋友给我写春联时,潞城正能量协会恰好打来电话,邀我参加一个“进社区、写春联、送温暖”的活动。虽然不擅长于舞文弄墨,但提前去感受一下那浓浓的年味儿却也是不错的选择。活动现场,只见有的裁纸、有的研墨,伴着书法老师们的笔走龙蛇,一瞬间,一条条春联写就,欢乐祥和的年味儿顿时便四散开来。在电视台的现场采访中,我还有幸成为被采访对象,自是在畅谈了手写春联的意义以及对新春的美好祝愿后,更是过了一把“上电视”的瘾。
是的,正如春节童谣里唱的那样,每一个时刻都有具体的事项,如今,在我的老家依然还是延续着这种传统的年俗。记得每每过年前回到家里,哪天磨豆腐,哪天蒸馒头,哪天炸丸子,哪天炸油条,都是要提前盘算好的。而老家的岳父由于有炸油条的手艺,所以每每临近年关为乡亲们帮忙都会一直持续到腊月二十八左右,而轮到自己家里总会排在最后,有时都无暇顾及。我和妻子也只能帮岳母和哥嫂蒸馒头、炸丸子、调肉馅、炖排骨等等,一项项议程丝毫不敢怠慢。
每每腊月二十八、二十九,随着村子上南来北往、大车小辆的日益增多以及在外游子的归来,村子上的年味儿更是达到了高潮。这时便挨上打扫院子、归纳整理琐碎凌乱的东西了,天地爷、祖宗灵位前的灰尘是需要打扫干净的,而摆放香烛以及上香的沙碗也是需要提前设置好的。
要说最过浓烈的就是除夕了,一大早,在吃过早饭后叫上儿子、侄子,搬上梯子,在我和哥哥的安排下贴春联,而贴春联似乎从来都是我的专属。毕竟,根据对联寓意哪副贴在正门,哪副贴在偏门对我们来说都是有讲究的。此时的妻子和嫂子,则是在和好面后准备开工包饺子了。除夕下午在挂好灯笼、垒起旺火后,就该上坟请先人们回来过年了。要说在农村除夕请先人们回家过年,绝对是一项非常有仪式感的年俗。为了让孩子们感知这一脉相承的家族渊源,每每上坟我总会叫上儿子们和我一同参与。拿上几柱香、几个天地炮到先人们的坟前先是磕头跪拜,再依次给孩子们介绍先人们的生平以及排序,嘱托他们不忘祖先,不忘过往。
是的,月是故乡明,情是故乡浓。每每腊月的忙年让孩子们一同参与,一同劳碌,一同感知,从而在亲力亲为中体验曾经的传统,感悟农村的年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这也许就是我对过年越传统、越“春节”的最好释怀吧。每每此时我总会想到王安石的那首《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今年过年,你回家了吗?(作者单位:潞城公路管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