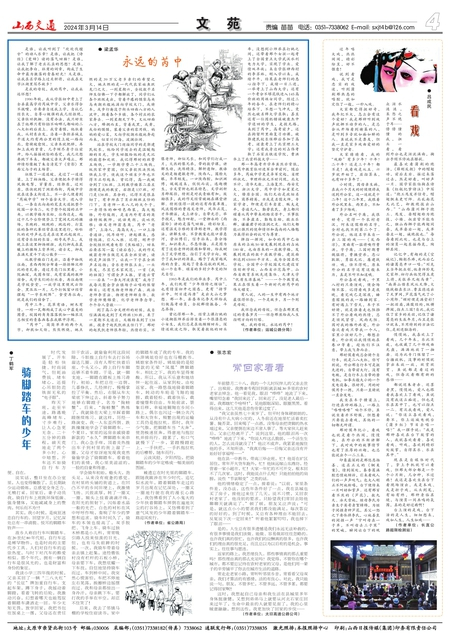看戏
吕成民
过年唱大戏,热热闹闹,精彩纷呈,好不惬意!
说到看戏,我可是忠实的戏迷,听到蒲剧那熟悉的唱腔,就如定住了一般,一秒入戏。
大家都觉得挺好奇,我年纪不大,怎么会有这个爱好?我是那种听到戏声就挪不动步的人,是总会从开场看到谢幕的人,是听到乡音就如痴如醉的人。虽说我不是票友,但我一直是家乡戏曲爱好的坚定守护者。
大家猜猜看,我的“戏龄”有多少年?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都不是!我看戏是从五、六岁就开始了,屈指算来,也有四十多年了。
小时侯,因母亲生病,在我六个月大的时侯便将我送到外公家,这一送就是十二年!这十二年里,我跟着外公风里来、雨里去,不知看了多少场戏。
外公名叫子廉,我很好奇,觉得一个农村老汉,何来这儒雅的名字,全村也找不到第二个了。外公说,他这名字来自一出三国的戏——《反西凉》,里面有一猛将唤作曹洪,字子廉,三国时期曹魏猛将,曹操堂弟,忠心耿耿、勇猛无比、屡建战功。哦,怪不得呢,原来外公的名字还有这般来历,真是不听不知道哦。
外公喜欢看戏,十里八村的只要演戏,便会场场不落。记得看戏多是夜晚,看完戏已是深夜,睡意朦胧的我一路睡到家。有时遇上下雪天,车子不好骑,就是推着走也阻挡不了外公看戏的热情,总是顶风冒雪、风雨无阻。因对我的格外疼爱,外公每次看戏只带我一个人,家里小孩好几个,都想去看,外公就让我悄悄地在巷口等着,趁他们不注意,带上我飞奔而去。
那时侯看戏总会骑个自行车,就是二八大杠,你可别说,外公那自行车可是挺先进的,自带前大灯,没有电瓶,是自行车上自带的磨电机,如拳头般大小的一个发电设备,很好用,用的时侯用手一摁,只要一直骑就一直会发电。
我坐在车子横梁上,行进在砂砾路上,一路上“咯噔咯噔”响个不停,虽说坐着并不舒服,但想着只要能去看戏,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
那时侯年纪小,看戏也就是看个热闹,慢慢地,在外公的不断讲解下,我对戏中的故事情节也有了浓厚的兴趣,也总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印象最深的是那惩恶扬善、追求正义的《铡美案》,情到深处,秦香莲满腔悲愤地倾诉,引来看戏人们的一声声叹气;包大人刚正不阿地断喝,台下便传来一片叫好和掌声。还有那百看不厌的《芦花》,数九天、冰天雪地,继母李氏为亲生子英哥身絮樟棉,为继子闵损身种芦花,其父一怒之下要休掉李氏,心地善良的闵损一声“宁叫母在一子单,不叫母去三子寒”的哭喊,瞬间让台下的观众泪水涟 涟 ,哀怨之声不绝于耳……懵懵懂懂 的我,扭头 一看,看到外公也是泪流满面,掏出手绢不停地在擦拭。
最喜欢看蒲剧的绝活,《薛刚反朝》中的帽翅功,前后左右、摇过来荡过去,煞是好看,叫好声一片。国学家张伯驹在诗集《红毹纪梦诗注》中写道:“跷工甩发并惊奇,帽翅飘来更可师。北乱南昆无此艺,却教绝技出山西。”“山西蒲州梆子跷工、甩发、耍帽翅称为绝技,小楼、叔岩皆不能为之,独山西梆子能两翅同耍,或单耍右一翅,或单耍左一翅,诚绝技也。”每每看到此处,也是与台上的演员一起东摇西晃,陶醉其间。
记忆中,有趣的是《空城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开口一唱:“刘先主当年把业创,他身拜卧龙定家邦。初行兵他凭得五虎上将,关张弟兄赵马黄”、“南屏山借东风从天降,火烧战船在长江。曹孟德逃出了天罗网,芦花荡气死了小小周郎。”顿时便是满堂彩!一把羽扇,满腹经纶,纵横捭阖,指点三国!自此,我记住了家乡的关羽,记住了诸葛亮的生辰年月,而且是张口就来,不用特别的方法记住,是刻进脑海的。
慢慢地,我喜欢上了看戏,几十年来,乐此不疲,也收藏了几十部戏曲光盘,满满地放了一抽屉。还为此专门保留了一台播放机,没事的时侯就拿出来放一放,欣赏欣赏,虽说都是看过的戏,但每次看都有新的感悟……
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慢慢地,爱人也跟着我喜欢上了看戏,虽说没有我这么痴迷,但也是乐在其中了,也可以指点一二。有次我看戏,爱人说:“你这么喜欢看戏,要不,你上运城电视台《蒲乡红》节目去唱一唱?”我一摆手说:“我是那种喜欢在台下鼓掌的人,我就喜欢看看。喜欢看戏、听戏,喜欢到精彩处鼓掌,自得其乐、乐在其中。”
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了,拿上手机就可以看戏,但那大部分都是一个个小片断,几分种,不过瘾!我还是喜欢坐在台下看现场演出,或是本戏、或是折子戏,从头到尾,有始有终,那种身临其境,与演员一同共鸣的氛围,真的是好过瘾啊!
台上演的是戏,台下活的是人生,细细想来,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作者单位:长直公路超限检测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