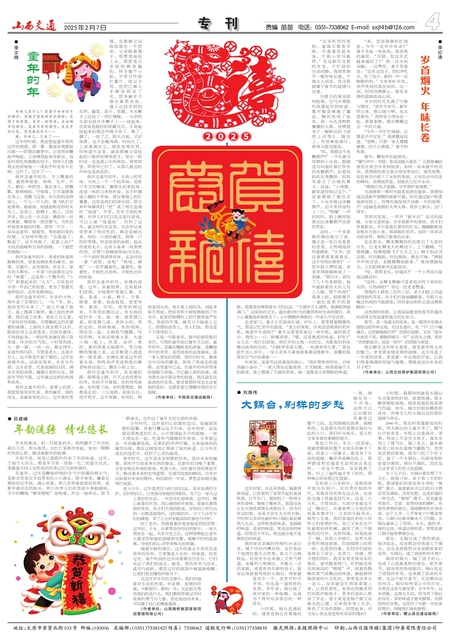大锅台,别样的乡愁
刘海伟
过年回家,车还未停稳,隔着两排房屋,已经看到了家里升起的袅袅炊烟。打开车门,便闻到了一股烤玉米的香味,像极了爆米花,那是母亲正在大锅里蒸馍头或蒸包子。因为只有这时候,母亲才会生大火用大锅,平时和父亲用电磁炉的小锅灶就足够两人生活。这种熟悉的味道,是温暖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更是母亲的味道,即使若干年后,我也能分毫不差辨别出的味道。
我的家在县城的西南约10余公里,属于汾河河槽沿线。也许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距主干公路较远,村里至今还未通上天然气管道,未被列入禁煤区。岁数大一点的家庭,或者有些年龄的房子,厨房还保留着传统的大锅台,我家就
是其中一个。虽然平时不多用,但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多年来,锅台成了我对家的一种依赖,也成为了我对母亲依恋的一种符号。
小时候,锅台是通炕的,通常是锅台在靠墙的一角,烟窗在另一个对角,这样可以让灶膛的热量穿过整个土炕,达到取暖的效果。最暖和的,也是最先热的是靠近锅台与炕的入口,我们叫火阁头,是儿时大家争着抢着睡的地方。
参加工作后,冬天一回到家,我就把脚插到置于火阁头的被子下面,再盖上一层被子,感受身下久违的温暖,懒洋洋地赖在炕上,那种舒适和安逸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一动也不想动。母亲做熟了饭,叫上三遍两遍才肯下炕吃,那种难忘的场景记忆犹新。
在村里上小学初中,是刚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实行责任制的年代,发展并没有现在这么快,先进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还是二八大杠,尽管如此,大部分家庭也不过一辆而已。去离家两三公里的学校基本靠步行。父亲的头脑灵活,做些小生意,我的家境比别的小伙伴儿们家稍好些,加上父亲在生产队就爱钻研机械,就找了两三个报废的自行车,东拼西凑,给我组装了一辆,供我上学骑行。虽然大部分零件锈迹斑斑,但抬腿跨上的那一刻,还是很自豪,在同学们面前是挣足了面子。在省力、快捷、图方便的同时,我其实更贪婪母亲的锅台。放学踏进院门,听到厨房里风匣抽动的“啪嗒”声,闻着热腾腾的蒸气里飘出的味道,就能猜到锅里放的什么吃的。常常是没多大一会儿,母亲就急忙将饭菜端上来,让我抓紧吃,免得迟到被老师罚站批评挨板子,更多的是担心耽误了学业,望子成龙是每个做父母最大的心愿。后来我未考上大学,辜负了父母的期盼,回想起来,对父母心里还是觉得有深深的愧疚!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大锅台生火做饭的时刻。浓烟弥漫,柴火噼里啪啦地响,锅里炖着的饭菜香气四溢。如今,城市的厨房精致却冰冷,再难寻儿时大锅台边的那份温暖与欢乐。
2000年,我在村里建新房的时候,用大锅台的人就不多了,煤气灶开始普及,年轻人注重清洁、省事,再加上不会生火底子,基本全用上了煤气灶。隔三差五,就有商贩用三轮车拉着煤气罐换气。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专门找了个好工匠,盘了一个大锅台,但厨房和卧室是分离的,锅台不通炕,因此也无法享受儿时的土炕温暖。
生下儿子后,大锅台着实帮了个大忙。按照习俗,孩子第三天的时候,要请要好的朋友和乡邻吃“展颜”旗子,寓意着孩子以后的日子都会笑容满面,没有忧愁,也是祈福的一种方式。“展颜”旗子,其实就是用葱花、芫荽、蒜等炒成的辅料,再放些煮熟的黄豆,调成酸味的长寿汤面。由于人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来参加,小锅小灶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大锅台就派上了用场,火大,盛的多,做的也快,味道还特别香,常常连着几锅才能将事情办完。
现在,大锅台成了我的牵挂。每次临走,母亲都会给我拿几个馒头,这也是我最想从母亲跟前拿的东西。大锅台,成了我别样的乡愁!
锅里的烟火,暖了游子的心,也成了心底最柔软的眷恋。蛇年春节,厨房里的热闹依旧,锅台见证了团圆的欢笑,也承载了浓浓的乡愁。在这个蛇年春节,无论脚步迈向何方,锅台始终是心中的归处,乡愁在这里生根发芽,岁岁年年,从未消散。这烟火人间,因为有了锅台的存在,家的味道才愈发醇厚,而那别样的乡愁,也化作了对新一年的美好期许,伴随我们奔赴新程。
(作者单位:稷山县交通运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