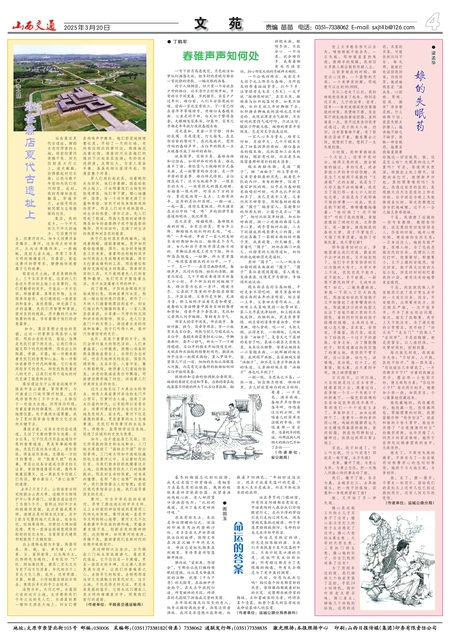娘的失眠药
梁孟华
世上大多数东西可以丢失,唯独睡眠不能丢失。一旦失眠,那种数星星的焦虑,数绵羊的烦躁,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数到怀疑人生。
以前爹娘在的时候,睡觉没心没肺,一个姿势到天亮,一个美梦笑到醒,那纯度可以达到99.999%。
自从二老走了以后,我的睡眠就逐渐差了起来,特别是近日来,儿子的法考、省考、国考……每到成绩深夜快要揭晓的时候,我便睡不着,坐在客厅胡乱地按着遥控器,直到凌晨一点,孩子过来告诉我考试通过,我才倒头入睡。然而,没有答案睡不着,有了答案还是睡不着,翻来覆去之际,就想到了娘,想到了一生失眠的娘。
小时候,我和爹娘睡在一个大炕上,经常半夜时分,睡得正香的我,就会被娘的抽泣,爹的叹息,或者爹娘小声的争吵给惊醒。或是为了大姐那不成器的“王满银”式的女婿,或是为了大哥久拖不决的婚事,或是为了我们那一家七口人的烂包光景,亦或是为了我那凑不够的学费……对此,我总是极不耐烦,嘟嘟囔囔地嚷着:“啥时候了?还不睡觉?”听到了我的烦躁,爹娘就像拉了闸的灯泡,立即禁言。我一翻身,继续做我的春秋大梦。我才不管他们,天塌了有爹顶着,地陷了有娘托着,我只管打鼾!
那年高考回村以后,爹娘望着比他们还高,戳在院子正中央的我,又开始犯愁了。他们辛辛苦苦供养的引以为傲的大秀才,大学大学上不成,农民农民不能当,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又该咋办呢?加之,二嫂突遭病故,爹娘一下陷入了巨大的危机,那滋滋啦啦的旱烟锅子又开始燎起了老爹嘴角的大泡,那装满活计的针线筐又扯出了老娘不眠之夜的无尽惆怅。看到同村同龄的孩子结婚的结婚,生孩的生孩,娘心急火燎,求东家,告西家,寻媒婆,找月老,就是为了给我找一个过日子的婆娘,安身立命。为了摆脱镢把子,彻底逃离这块我厌倦了的黄土地,我依然不管不顾,没心没肺,该吃吃,该喝喝,卖冰棍,打小工,挖果窖,贩水果。白天累的半死,晚上睡得像猪!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大自然就是这么亘古有序。随着星隐日出,寒暑过往,在爹娘一个又一个失眠日子的拼凑下,一幅色彩斑斓的农家命运抗争图逐步展开。等到我们一个个成家立业了,爹娘却老了,油水也被榨干了。老黄牛一样的爹终因心梗,残缺的腿脚再也无法支撑他那羸弱的躯体,轰然倒塌,倒在他那耕耘过,播种过,收获过的那片黄土地上。
至此,我才知道了,什么叫长眠,什么叫安息!那就是一睡不醒,永不失眠!
老爹,撇开了娘,与青山为伴,与黄土为伍,把一大堆人间操心的烂事丢给了娘。
我们,撇开了娘,各自为巢,去城里打工,去异地谋生,把一院子的孤独、寂寞和一身疾病留给了娘!
娘,又开始了另一种失眠。
操心在运城工作的小儿子买房子了没有;操心在北京打工的侄子生活稳定了没有;操心大姐的水果生意、大哥的化肥生意、二哥的门锁生意,操心她的孙子、孙女们找到对象了没有?
为了照顾年迈的娘,我们姊妹几个给家里装了监控,手机24小时待机,随时听候老太君召唤。隔三差五,姊妹几个给钱的给钱,送药的送药,买菜的买菜。可娘依然闷闷不乐。每礼拜,娘就打电话招我回家,向我诉苦,她说她现在是“高血压、心脏病、胃病、眼疾、腿疼”浑身都是病,什么病都不怕,就是失眠太折磨人;她说她不缺吃不缺穿,就缺一种安眠药。她要求我每星期要给她送一回安眠药。娘,这是怎么啦?失眠真的这么严重吗?可是,每逢周末夜深,陪娘在土炕上聊天,话题尚未打开,娘便鼾声四起,真的需要喝药吗?为此,我通过家里的监控,发现娘大白天总是在炕上和衣而眠,似乎就是为晚上失眠做准备似的。每次我都通过语音把她喊醒,过不大一会儿她又昏昏欲睡。
于是,我请教了运城的一些专家教授。教授告诉我,说是要经常回家陪陪老人,你在的时候,她有心理依赖,便能睡的安然无恙;一旦身边没人,她就失眠严重,很难入睡。为了完成老娘交代的任务,我便托人四处打听,效果要好,刺激要小,又不上瘾的安眠药。每次回家,娘不再关注我的大包小包,而是时时刻刻盯着我的口袋,看有没有给她带来安眠药。
于是,到医院找熟人开安眠药又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一大艰巨任务。因为,开安眠药,必须要有处方,而且极其严格,一次不能多开,开多了医生怕出问题。每次,娘见了我都要,我手上又不能没有。为了满足娘的日常需求,我开始了“动关系”“走后门”“找熟人”“求同学”,不是拍胸脯,就是发誓言,以人格担保,一定管好药粒,控制剂量。
每次娘见到我,我就故作无奈:“不好弄,人不熟,医院不给开。”娘一脸失落:“你这娃这几年瞎混了,一片药都买不下!”当看到我摊出双手,露出那一小包药片时,便又转怒为喜:“你这坏小子!”每次药片到手,娘都如小孩一般,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娘收藏她的,我收藏我的,她收藏一包,我收藏两包,等娘需要的时候,我便装模作样“待价而沽”。就在和娘的斗智斗勇中,娘也许厌倦了“长夜漫漫何时旦”的痛苦煎熬,也许厌倦了人间药片的苦涩难咽,她终于在奔赴运城看望我的途中,无疾而终。
娘走了,不再有失眠的痛苦,不再有为了一粒安眠药而煞费苦心的急切切等待,她终于与大地长眠,与爹相伴。
娘,走了,摆一摆手,不带走一粒药片,留给我们的是炕头上还有几包已经过期的药片,还有人间无尽的忧伤。
(作者单位:运城公路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