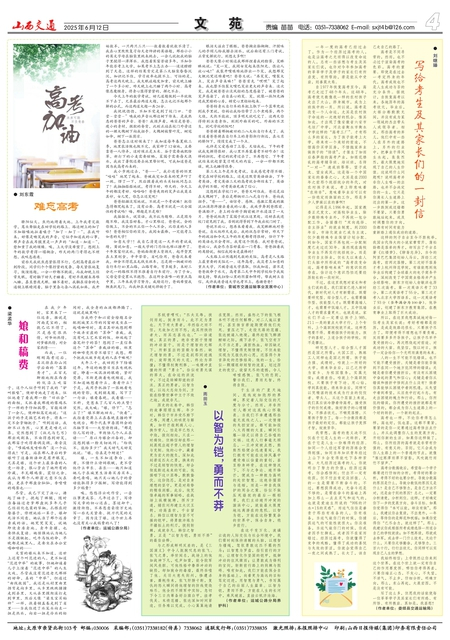娘和稿费
梁孟华
在我少年时,家里来了一位远亲,据说是河南灵宝的,相貌已记不得了,只是感觉很热情,对爷奶热情,对爹娘热情,对全家热情……
而我,一位刚刚高考过后,名次排在孙山同学后面的“落第秀才”,正百无聊赖地爬在西房的炕沿上吹笛子,这个人似乎听到了我的“驴叫狼嚎”,便好奇地走了进来,怔怔地看了看我那一脸“旧社会”的面相,又抓着我那瘦的像鸡爪子一样的手仔细揣摩,百般端详了一会儿,便神秘笃定地说:“这孩子的手是搞艺术的手,将来一定不会拿锄把子。”听到这话,我却不以为然,心里更是嗤之以鼻,突然想到了《状元与乞丐》那出戏剧来,不由得感到好笑,我那笛子吹得要调没调,要音没音,“哆瑞咪发嗦啦西”没一个认得我!可是,站在那人身后的爹娘听了这番断语却是眉开眼笑,尤其是娘,这个世上最吝啬的人竟一转身,狠心拿出了她所有的珍藏,半瓦罐鸡蛋,震惊之余,我认为那个人醉翁之意不仅在酒,更在乎那盘金灿灿,香喷喷的鸡蛋也……
尽管,我已下定了决心,撸起了袖子,挽起了裤腿,随时准备接过老爹那盘玩多年几乎已经羽化包桨的犁柄,扎根农村娶婆子,修理地球一辈子,娘却死活不同意,她认准了那个远房亲戚的话,她哭哭笑笑,说她即使卖房卖地,卖牛卖骡,也要供我复读。她倔强地认为她儿不是摸镢把,吃牛马饭的命,早晚都是城里人,是要坐在办公室喝咖啡的……
文盲的娘从来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个叫范进的人,更不知道“范进中举”的故事,但她却逼着儿子上演着“范进中举”的人生大戏,尽管我没有范进老兄那样的好命,真的“中举”,但通过“曲线救国”,我还是从村里曲里拐弯走向乡里,从乡里跌跌撞撞走到县里,又从县里摸爬滚打走到市里,然后又像“梁生宝买稻种”一样,挟着铺盖卷走到了省里……当我住进了水笼头向左一扭是热水,向右一扭是冷水的标间时,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这就是城里吗?
当我终于和以前金榜题名分配到城里工作的同窗好友坐在一起喝咖啡时,莫名其妙地想到那个故弄玄虚的“算命”亲戚,我没有吃上艺术家的饭,却端起了耍笔杆子的茶!想到了一直信奉这个“算命”亲戚话的娘,杯里的咖啡竟然苦不堪言!我想,那个把我从故乡赶走的人在干嘛呢?
大年三十,我回到乡下陪娘过年,年迈的她整日坐在电视机前,睁着一双混浊的眼睛,紧盯荧屏,不断更换着电视频道,我不知道她想看什么,要看什么?于是,我用手机拍了一张她看电视的背影,发到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娘看春晚,我看娘……不料,竟惹来了几百人的点赞!突然,我大喊:“娘,停下”。“怎么了?”娘不解地回头,“快看”,我指着荧屏上正在春晚直播的市电视台,那个代表市委团拜会的压轴节目——大型诗朗诵,“那是你儿写的诗,市朗协几个人正在读……”原以为娘会兴奋的,却没想到娘一脸关切地问:“给钱不,能给多少?”我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娘,你真是个财迷!”
娘,一生不知道李白、杜甫,不懂什么诗词歌赋,更不管他什么市长、县长……她只知道她儿子在城里生活要买房买车,要吃要喝,她只关心她儿子的劳动能取得多少报酬,写诗能得到多少稿费?
唉,悠悠浮云吹作雪,一壶往事煮成茶。几年过去了,写诗写文章的初心还在,墨迹却干,激情渐隐,不再愿意豪情万丈地写一些无关紧要、捉刀代笔的文章了。因为没了娘,这个世上再也没有关心我稿费的人了!
(作者单位:运城公路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