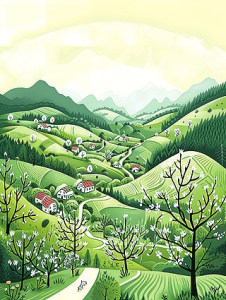缺水的村庄
刘东霞
我老家位于太行山腹地,沟壑纵横,干旱少雨,小时候印象最深是村里吃水困难。村里没有井,唯一可以蓄水的地方是村边低凹处的一个泊池。夏天暴雨来临,全村的水顺势而流,都集聚到泊池里。泊池里的蓄水能够人畜饮用一到两个月,除此外的时间泊池干枯了,人们就不得不到外村挑水吃。
那泊池的水实在太脏,村里的垃圾、泥土、牲畜粪便、树枝草叶都流到泊池里。第二天,泊池水面上漂浮着许多棍棍棒棒和树叶草叶,村委组织人用长笊子把这些漂浮物捞出来,两三天后泊池里就是半池绿水。就这,村民也高兴,终于有水吃了!
这样的时间延续不长,过了暴雨期,泊池里蓄不上水,水量只减不增,慢慢就干涸了。
村里没水了,人们天天要用水,水贵如油,一滴也不能浪费。记忆中,洗菜水和洗锅水拌猪食,早上洗脸水舍不得倒掉,存在脸盆里,一天都可以洗手,晚上再洗脚,一家人都用这半盆水洗脚,最后一个人洗过后已成了差不多露出盆底的又黑又臭的脏水,但还舍不得倒掉,用来和煤。一盆水真是用到了极致,谁也不要笑话谁,家家如此。至于洗衣服嘛,冬天的棉衣,春天的秋衣和外套,都要放到夏天泊池里有了水才洗。曾听过一个笑话,村里缺水,早晨起来两口子互相往对方脸上唾吐沫洗脸,当然夸张了,不可能的事情,但也说明了水的十分珍贵。
村里没水,村民吃水就到外村挑。去两个邻村挑水,一个较近的离我村三里,但路不好走,窄窄的土坡路,去时下坡回来上坡。另一个离我村五里,路较平坦,也宽阔,可走马车。
一般村里人愿意去较近的那个村挑水。白天下地哪有时间啊,只有下午收工回来,用稀糊糊填填肚子,就算吃了晚饭,然后挑起两只水桶,晃悠悠往村外走。这口井供应周边三个村子的人吃水。秋天,由于夏季雨水多,井里的水旺,冬天和第二年春天,井水就少了,尤其是春天干旱时,井里出水细细的一缕,半天才能一桶,在上面打不起来,人就下到并里一勺勺往桶里舀,一晚上能舀两三担水,还得排队,那些没劳力的人家就买水,一毛钱一担。我十一二岁就跟着大人去外村挑水,桶里水不满,水离桶沿还有一巴掌高的距离。我把扁担放到肩上,桶挨着地拎不起来,只好将扁担两头的铁链子绕着扁担,一个顺时针一圈,一个逆时针一圈,这样缩短了铁链与桶的距离,又能保持住平衡,就可以拎起桶。我这样挑起水桶,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在坡上缓慢走,汗水从脸上流下,滴在脚下的土路上。我不能歇,也不敢换膀。有一次上坡中间换膀,没掌握好平衡,扁担脱落,两只水桶滚到旁边的地沟里,水洒尽了。上坡后是平路,才可放下担子歇脚。为这井水,那个邻村的人曾不止一次与外村人发生口角和打架,想阻拦外村人去他村挑水,但邻村是个只有四五十户的小村庄,周边的村都比他们村大,村民惹不起。不止一次,邻村村民与外村人打架,外村人一哄而上去了许多人,人多势众,邻村人害怕,只好作罢。
我也曾去较远那个村子里挑过水。路远,路平,中间歇四五次才能到家。
夏天,大雨来了,家家户户的门外摆了一溜锅碗瓢盆缸缸罐罐,能用的工具都用上,接从屋顶瓦楞上流下的雨水;冬天,地上有了积雪,人们小心翼翼铲起干净的积雪化水。
上世纪八十年代看电影《老井》,电影里祖祖辈辈缺水的场景与我村的一模一样,真实情况确实如此。去年“七一”节,单位组织去红旗渠参观学习,看到林县人民曾经吃水困难的情景,我的眼泪涌出来,我童年的经历与其很相似。那是刻在心里的磨不掉的记忆!
后来为解决吃水困难问题,政府组织给我村送水。大卡车驮着一只硕大的水箱,一进到村里,全村人欢呼,比过年都高兴。老头,老太太,大人,小孩,挑着拎着水桶往车跟前跑。大家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放水员将长长的管子伸到自己桶里,脸上绽放出花朵。
年三十,是最忙的一天,家家户户迎祖,贴对联,架年火,搭喜棚,最重要的还要去外村挑水。老家的风俗,大年初一男女老少不干活,一干活就把这一年的运气干跑了,你这一年就不得清闲,劳苦受累一年。当然是迷信的说法,但是村民们还是蛮讲究的。因此,年三十这天家家户户存些水,起码够初一用一天。那挑水的队伍蜿蜒在窄窄的乡间小道上,扁担“咯吱咯吱”不绝于耳,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挑水队伍,蔚为壮观。有一年的初一,父亲早晨起来吃过饺子后,从屋里到院,再从院到屋里,出出进进几次都不知道该干啥?平时劳动惯了的父亲,一闲下来浑身不舒服,觉得没意思。最后,父亲拎起门后的扁担和水桶往外走,母亲拽住父亲问,你这是干啥?父亲说,乘今儿是初一,没人去挑水,我去挑,井水肯定旺,用不着排队等很长时间。母亲哭笑不得,半嗔半怒,你神经病不是?家里的水够吃两三天呐,可父亲哪听得进母亲的话,还是挑着水桶出门了。近中午父亲才挑着水桶一瘸一拐走进了院子。父亲的衣服上湿了一大片,还沾着泥巴。前一天的水滴在地上结了冰,父亲进村口的下坡路,没注意踩到冰上滑倒,两只水桶顺势滚到坡底,桶里的水全部洒完,父亲的脚也扭伤了。“唉,我真不中用。”父亲一股劲儿埋怨自己,望着满脸通红,有些羞愧的父亲,母亲和我流下了眼泪,一串串,流了许多。
后来村里接上了自来水,没水吃的日子成为历史。对于这个百把户的村庄来说,开始了亘古未有的新纪元。夜幕降临,村庄亮起星星点点的灯火,此起彼伏的水流声从各家厨房传来,混着炒菜的香气在街巷飘荡。曾经闲置的老井被改造成景观池,井底铺满鹅卵石,水面倒映着孩子们举着水枪嬉戏的身影,与新矗立的水塔交相辉映,诉说着日子里新的希望。
(作者单位:晋城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