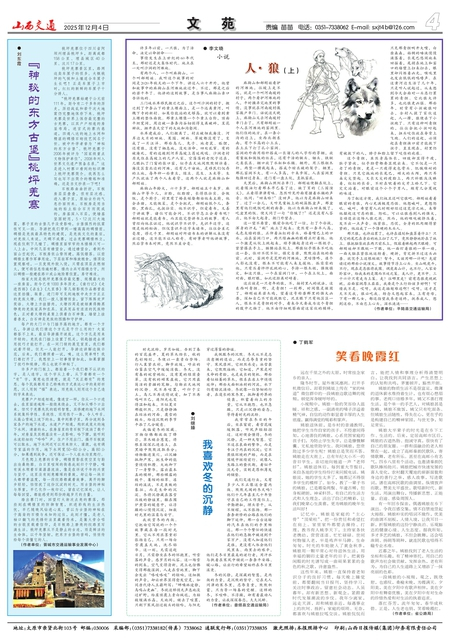小说
人·狼(上)
李文晓
许多年以前,一只狼,为了活命,决定以命拼命……
事情发生在上世纪的60年代末,那时还是大集体时代。地点在一处叫沙涧的河滩地。
有两个人,一个叫麻驹山,一个叫郝刚娃。我听这个故事的时间是202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讲述人六十开外,他曾和故事中的麻驹山在河滩地放过牛。不过,那是之后的若干年了。他讲的这则故事,是当事人麻驹山亲口告诉他的。
三门峡水库移民搬迁之后,这个叫沙涧的村子,搬迁到了中条山下的黄土塬面上,是一个远离黄河,叫槐下寺的新村。如果你能站的足够高,就可以看到黄土塬的整体面貌。那黄土塬像一个个黄土台阶,顶面平坦宽阔,周边被一条条沟谷切割得支离破碎,呈花瓣状,摊开在天空下的大地和沟壑间。
水库建成后,人们搬离了,村庄被彻底淹没。河岸边大片的田地、果园、树林、草坡都没有了,变成了一片汪洋。那些鸟儿、兔子、地老鼠、狐狸,还有狼,没有了栖息地,没处活命,四处乱窜。有的被淹死,有的逃避到河岸高坡上苟延残喘。沙涧老村原先住在高坡上的几户人家,空荡荡的老院子还在,几眼扒了门窗的张口窑,似乎在天地间默默倾诉着。淹没区靠北边的河滩,还有几十亩地,是移民们仅存的土地,每年种一些黄豆,绿豆、花生、玉米等。生产队就派了两个人来看管,这两个人就是麻驹山和郝刚娃。
麻驹山年龄大,六十多岁,郝刚娃五十来岁。麻驹山中等个儿,方脸,红脸膛,长得很壮实。会做饭,是个厨子。村里有了婚丧嫁娶都由他来主厨,他会杀猪,又能做菜,是个全把式。郝刚娃低个儿,条脸,黑面孔,也挺壮实。他不识字,但爱看书,又善于讲故事。诸位可能会问,不识字怎么会看书呢?郝刚娃就是能看书,而且能完整讲书上的故事。有人曾经向他求证过,他说识字不识字,先识半边字,这便是他的秘诀。但仅靠识半边字来读书,往往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郝刚娃对所读书本的讲解从来没有出过错,这不能不让人称奇。有好事者听他讲故事,然后拿书本对照,竟然不差分毫。
麻驹山和郝刚娃看护的河滩地,往坡上走不远,就是一个叫河南坡的村子,两个看护河滩地的人,平时操弄完地里的事情,没事就在河南坡村挨家挨户串门。话说这天晚上,麻驹山又去河南坡村串门去了,只有郝刚娃一个人在河滩地的窑洞里。他们住的地方,在一条小沟的边上,坐西北朝东南,有个不高的小土丘,在土丘下打了孔小窑洞。窑洞的外面用秸秆搭成一长溜儿的人字形的茅棚,放有案板和做饭的灶具,还有干活的镢头、锄头、铁锨之类农具。棚口放了水缸和水桶。棚外,用三根粗木杆,两竖一横栽起来,搭成个晾衣被的架子。棚里,那孔窑洞不大,有一人多高,十来步深,人在窑洞里勉强回过身来。进门有一盘土炕,直抵窑底。
天黑后,麻驹山照例去串门。郝刚娃便躺在炕上,就着煤油灯看那本早已卷了边、缺了页的《三国演义》,正看得津津有味。忽然听见外面有撞着水桶的声音。他问:“回来啦?”没回声,他以为是麻驹山回来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案板上的碗筷瓢盆声,那盆里有他们晚饭吃剩的面条。他以为麻驹山回来饿了,吃盆里的饭。便又问了一句“你饿了?”还是没有人答应,他不由欠起身,朝门外望去。
这一望不要紧,眼前令他吃了一惊,打了个冷战,浑身的汗毛“刷”地立了起来:竟然有一条半人高,毛色灰暗的狼,正伸着血红的舌头,舔着嘴巴上的口水,站在窑洞门口,两只绿幽幽的眼睛正盯着他。他一个激灵从炕上跳起来,顺手操起身边的一根棍子,紧紧攥在手上,猫腰站在炕上。那狼似乎根本不吃他这一套,依旧不慌不忙,镇定自若,默默站在他的面前。此时,窑洞外是荒野的河滩地,黑咕隆咚,连个人影也没有,根本不可能有人来支援他。孤零零的他,只有压着怦怦乱跳的心,手持一根木棍,强做镇定,和这只狼,一个在窑洞门口,一个在土炕上,面对面,眼盯眼,如此近距离对峙着。
这应该是一只老年的狼,不,按村里人的说法,这东西叫青狈。啊,是青狈!一刹那,时间像是凝固了,郝刚娃呆若木鸡,望着这号称兽群里的强大凶兽,深知自己不可能战胜它,况且眼下只有他区区一人,根本不是青狈的对手,看来今天要成为这个青狈的腹中之物了。他不由仔细观察面前这家伙的模样,
只见那青狈咧开大嘴,白齿森森,粘稠的唾液慢慢滴落着,长尾巴悠闲地来回摇着,尾梢在地上和窑口的墙壁上扫来扫去,眼里却闪烁着凶光,喉咙里也发出低低的呜噜声。在这黄河边生活了几十年,只是听人说起过,从未想到今天会面对一头恶行累累的青狈。它比狼大许多,也比狼更凶猛。那些年,时常有小孩被狼叼去,全村人提了家伙追赶,人一撵,狼便丢下小孩跑了。只有这种叫青狈的,往往会把小孩叼起来,扭头咬住放在脊背上飞跑。人们的追赶,必须赶在青狈换口前才能救下孩子。直至现在,村里仍有被救下的人,脖子和脸上留下咬伤的疤痕。
这个青狈,虽然身高体长,四肢却显得干瘦,肚子紧收,似乎肋骨都要显现出来。它不仅是一只老了的青狈,更是一只瘦得皮包骨头、饥饿难耐的青狈。只见它拖地的长尾巴,硕大的头颅,两只耳朵尖尖竖起。又长又尖的瘦脸上,两只斜眼浅浅眯着,红红的长舌,不时在呲着的尖牙上舔几下。它定定站着,对眼前这个小个子男人,颇有几分蔑视的味道。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权且还叫它狼吧。郝刚娃看着眼前的老狼,内心充满极度恐惧。他想喊叫,更想怒吼。喊叫,希望有人此时刚好经过这荒凉之地,来帮他驱赶这可恶的狼。怒吼,可以让狼感到人的强大,自动退出这场人狼之战。然而,他的喉咙被挤压着,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紧张,恐慌,全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他站成了一个僵硬的木头人。
那只狼,也许站累了,也许在谋划和盘算着什么?只见它的尾巴在身后的地上扫了几下,竟然静静地卧在了地上。狼把脑袋放在两只前爪上,假寐着眯起两只眼睛。可郝刚娃却不敢眨一下眼,他一面盯着狼的一举一动,一面大脑在紧张地运转着。硬拼,肯定拼不过这头凶兽。就凭手上这根短棍?智斗,又该用哪一计呢?先前读过的那些小说演义,故事情节浮上心头。坐山观虎斗,不行,现在是恶狼将我围。调虎离山计,也不行,人家安卧窑口,给我来的是围而不攻之策。美人计,更不中。三十六计只有走为上策。走?往哪里走?前有恶狼虎视眈眈,后面窑洞厚土层层,我要是个土行孙该多好啊!可惜我不是。哎呀,我这是插翅难逃啊!哎呀,这才是天不灭我,狼必吃我。转念又想起家来,上有老母,下有一群儿女,都还指望我养老送终,抚养成人。想到这些,不由悲上心头,泪水涟涟……
(作者单位:平陆县交通运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