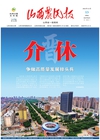他们把自己根植于大地
当我把眼前这一沓厚厚的报纸翻完,我的内心受到了久违的冲击。就是这么一群人,走遍山西59个县(市区)的101个村庄,集体或分头住村采访累计天数超240天,行程超过8万公里。就是这么一群人,见证了全省5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7993个贫困村步入小康的全过程,记录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乡村巨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记者,他们属于同一个集体——山西农民报。
在大多数人的固有印象里,记者主要是“摇”笔杆的。本可以坐下来安心“摇”笔杆的一群人,为何要讨苦吃、找罪受?首先源于《山西农民报》的优良传统和精准定位。作为一份与共和国同龄、由毛主席亲自题写报名的报纸,如何办出特色、走在全国农民报前列,是每任报社领导殚精竭虑所思考的。
在确定了“小人物、接地气、暖新闻、正能量”的办报宗旨后,怎么样践行就成了重中之重。报社地处太原市区,远离农村,大部分编辑记者在城市中长大,农村生活经验几乎为零——怎样在一个城市化、网络化了的时代中始终保持和农业、农村、农民的鱼水关系,是关系农民报发展的大事。那么,只有把自己沉下去,只有主动拉近和农民的距离,只有先把自己变成“泥腿子”,只有狠狠心了……于是,长达9年的住村采访开始了。
听见自己生长拔节的声音
记者柳飞与我同龄,已有10年工作经历。谈到第一次住村采访时,路上大雨滂沱,泥泞不堪,他的话语中没有一丝不悦,反而充满了快乐。说起当时的三晋微商第一村,和时任第一书记的接触,村民们新潮的行为怎样震撼着他年轻的心灵,我似乎能感受到电话彼端按捺不住的兴奋。岚县一位脱贫户的经历,让他深深地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是何等重要。
柳飞从11岁就来到太原,直至住村采访之前,他都没有和农村、农民打过什么交道。凭着一腔热血和工作激情,他深扎村野,最开始是咬牙坚持,到后来成了轻车熟路,乃至乐在其中。烈日曝晒、蚊虫叮咬忍着,听不懂方言就一遍遍地听,三番五次采访才能写出一篇有生活气息的报道……
这一切都和他想像中的记者工作不太一样了。但也许每个记者骨子里都有亲近自然和泥土的天性,渐渐地,柳飞在9年的住村采访中,见证了农村的变迁。喜欢上农家饭的香、农民的淳朴和农村的田园风景。10年的工作经历里,柳飞有9年都跑村、住村,他说这9年自己成长得特别快,就像一棵小树,在最合适的时候得到了来自大地的滋养,于是不停地生长、拔节……
急切地奔赴下一个现场
记者金建强,人称“老金”。于1995年来到报社,一干就是三十年。三十年里,“小金”变成了“老金”,发际线不断靠后,工作经验成倍增长,成了报社里人人称赞的“农业记者”。老金喜欢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写好农业新闻对他来说不仅是职责,还是志趣爱好,更是崇高的追求。老金写了很多好稿子,新近的一篇是发表在《农民日报》的特稿——《住村记》。
提起住村,他回忆起那一次:像是一次奇遇,又像一次历险。他说,2016年6月上旬,他和柳飞开车奔赴武乡县南关村采访,路上突降瓢泼大雨,黄豆大的雨点乒乒乓乓敲打着车窗,当时能见度不足20米,但一直没有停下来避避雨。只因为他们与村里的采访对象约好要中午前赶到。
这样的突发情况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可他硬着头皮大着胆子,用了7个小时才跑完170公里的既定路程,到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多。
采访当然爽约了,但村民们还是很热情招待了他们。吃了一碗面,他们马上就开始走访,到深夜才回到住处。村委主任夸他们说,“像你们这样的记者,俺村还从来没来过”。
“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过记者光鲜亮丽的一面,没有看到我们狼狈苦累的一面,但我们苦中有乐,累中有甜。”老金淡淡地说。
记者很忙,忙到什么程度呢?我好几次约老金谈谈采访经历,他都抱歉地说没有空。一年365天,除了法定节假日,他们基本没人会请假,因为工作量大、工作节奏快,如果有一人请假,那么工作量就会转嫁到别人身上。年轻记者一个星期中有三到四天在外采访,闻风而动、随时待命。只要得到命令,不管是睡意正浓的午后,还是寒风刺骨的午夜,他们都得马上行动。
就在采访前一天,老金他们还在忙农民丰收节的相关报道,凌晨一点多才下班。记者累,老金等几个部门主任尤其累,不仅是因为他们几个人都身兼多职,还因为他们想把《山西农民报》办成全国最好的为农民服务的报纸。
有追求就会有压力,但压力也会转化为动力,所以急切地奔赴,是老金他们最鲜明的性格特点。
别样的风景
记者曹鑫睡眼蒙眬地向远处看,这种从未见过的风景让她瞬间清醒了:在茫茫如夜空一样深邃无垠的黑暗里,闪着星星点点的光芒,那是什么呀?那不就是乡亲们戴在头上的采摘探照灯发出的光吗?她进而想到,一点“星光”下就是一张全神贯注的脸,一双勤劳朴实的手,一颗期待好收成的急切的心。千千万万的“星光”,就是千千万万个农民的化身。这光亮堪比天上的星星,这是伟大的、壮观的劳动场景;这光芒比天上的星星更耀眼,因为它们不只闪耀在眼里,而且闪耀在心间。有一种类似电流一样的东西瞬间击中了她的心,在城市长大的她,又一次发现了乡村和田野独特的美。
曹鑫说,从那一刻开始,她完成了心灵的嬗变。她说不清是为什么,可能只是她内心中不曾被发觉的关于农村的印象被推翻了。
在另一个晚上,记者张美丽也被震惊了,只不过她的表达方式不是张大嘴巴,而是泪流满面。
74岁脱贫户的一生如同一部电视剧在她眼前演绎:老伴因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儿媳妇因病去世,欠下十几万元的外债;二孙女罹患先天性心脏病,12岁时不幸在她怀里离开人世……老人坚强地撑起这个家,在当地干部帮助下开起农家乐,当上了村里保洁员。
老人的苦难令张美丽深感命运的不公,老人的坚强又让她感叹中国农民的坚韧。政府的帮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勇气和毅力——张美丽在老人身上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之后张美丽一直思考,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自己该做些什么?
她终于找到了答案,把住村采访深入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023年12月6日,张美丽第三次来到大泉山村,已经81岁的郇桂英喜出望外,拉住她的手不愿松开:“闺女,现在日子好哦,给你算算我家今年的收入账……”
临走时,张美丽掏出200元钱,硬塞给了郇桂英的老伴钱巨。钱巨将一个大红苹果摁在张美丽手心:“闺女,路上解渴吃。有空就来家住上几天。”
曹鑫和张美丽,通过发现别样的风景,找到了自己职业和人生新的赛道。
果子结在树枝上
经年累月地奔走跋涉,让记者们的腿瘦了,脸黑了,但精神头儿更足了,写出来的稿子更耐看了。住村采访是对乡土中国的触摸和解读,这样的解读必然是深度的、独特的,那么农民报的编辑记者在省内外新闻评比中多次获奖就是意料中的事,2017年农民报记者集体采写的住村采访特刊——《走进贫困村》荣获全国农民报特等奖。
9年的住村采访,让山西农民报的编辑记者们交了一大群农民朋友,每个人都有了“农民朋友圈”。基层党员干部亲切地称呼《山西农民报》为“咱报”。
树干茁壮,果子才能鲜红饱满。而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的根扎得足够深,根系足够壮。他们不做空中翻飞的鸟儿,也不做林间敏捷的兔儿,他们甘愿做一株株农作物,把自己植根大地。他们守护大地,大地也以更博大的胸怀接纳他们。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山西农民报记者。
卓一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