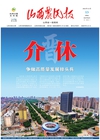故乡的土炕
近日,故乡邻里老人过世,我在事主家忙乎了一个星期。此时,正值数九寒天,虽然开了热风机,睡觉时被窝里仍冰冷得腿都不敢伸。第二天,我便用柴火将新盘的土炕烧起来,睡在上面,整夜感觉身上都是热乎乎的,心中不由得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我是在土炕上出生的,土炕有我童年快乐的记忆。土炕,在故乡人的眼里如同天堂,乡亲们在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后,晚上躺在土炕上酣然入睡,在土炕上繁衍后代,在土炕上喜怒哀乐,又在土炕上慢慢地老去。土炕与庄稼人的日子密不可分,不仅是躺卧睡觉取暖之地,更是体悟生活滋味,涵养殷殷亲情的场所。
土炕源于哪朝哪代,无从考究。但我知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多数的人家都盘有一面、或几面宽大敞亮的土炕,大都占据了近乎半个房间,成为故乡人生活起居的主要舞台。
土炕最大的优点是花钱少,砌垒容易,冬暖夏凉,睡着舒坦。它看似简单,可不是一般人都会打造的,绝不比制作一张席梦思床容易。农村人通常在房子建好后就开始打造土炕,也习惯叫“盘炕”。盘炕有“盘”的讲究,要紧挨门窗,两边或三边与实墙连体。“盘”的时候,要先用土坯(老家人叫胡基)和泥浆砌垒出若干个立腿,在立腿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间,烟火通道的走向像蟒蛇一样盘来盘去,占满整个炕面。接下来根据炕面的大小,在炕沿下方留一个或两个炕口,用以添加柴火。整个框架成型后,在立腿上用“泥基”来铺炕面,再在上面用泥抹子抹上麦秸泥,薄厚适中,均匀平展,做到既能承受住孩子们在炕面上蹦蹦跳跳的压力,还能耐得住高温下的柴火烧烤。盘土炕时火道烟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考验着工匠的技艺,好炕既节约柴火,又满炕暖和,炕边还不漏烟。
2008年,我将老宅拆除建成新厦后,请了位技术高超的盘炕师傅,在新房盘了火炕,一面靠窗,两面靠墙,炕的前面和整个房间全是白瓷砖贴面,美观大方,十分漂亮。这种炕与老式炕相比,结构更加合理、科学,主要性能是通风、利烟,热能利用率高,烧炕时屋子里没一丁点烟味和灰尘,还能把满屋子都烤得热烘烘的。
如今,盘炕的“泥基”已经没有人做了,乡亲们开始用水泥制作的预制板代替,水泥板没有土坯泥基那样冷热宜人,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传统的老土炕,土炕的土腥味里混合着世事伦常的味道和人间烟火的气息。
记得小时候,家里条件非常艰苦,盘的炕没有炕沿和护栏,炕面上铺了张芦苇席,炕墙没有装饰,几张报纸当作“围裙”。一烧炕,烟火伴随着土腥味直钻鼻孔,让人真正体会到了土炕的“味道”。现在村民的日子富裕了,虽然还睡在土炕上,但装饰得非常“豪华”,炕面用水泥涂抹,炕沿换上了一寸厚的实木、石材,或用瓷砖做炕沿,看上去十分喜庆美观。最为明显的是炕面上多了价值不菲的毛毯,薄厚适中的褥垫和鲜艳的床单。虽说睡在上面软绵绵的不硌人,但总觉得少了点儿时那种烟火泥土的气息。
故乡的土炕,大多连着做饭的灶膛,俗称“锅连炕”。灶膛可以烧火做饭,土炕可以取暖,既做了饭,又烧了炕。一日三餐,灶膛的烟火顺着炕洞绕来绕去,炊烟从屋顶上的烟囱里涌出来,流向天空,飘向远方,成为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如果遇到寒冷的天气,晚饭前再用苞谷秆或玉米芯之类的柴火加烧一次,炕的热度可以保持到天明,一家七八口人偎依在土炕上,被窝里总是暖暖的,任屋外寒风呼啸,毫不在意,说说笑笑,酣然入睡,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温暖的。
记忆里小时候的冬天,雪总是下得很大,感觉特别寒冷,烧土炕是母亲最操心的家务劳动。母亲常常收拾了锅头,喂了猪,然后抱回柴火烧炕。柴火多是一些庄稼秸秆,既不能放得太多,也不能放得太少。多了造成浪费,炕太热烫得没法睡,还容易引起火灾,太少则炕热不起来。为了保持炕温,烧完炕后,母亲再从柴草堆里揽回些麦衣或碎柴末,用双手捧起一点一点地塞进炕洞里,随后将炕门盖上,再用棉絮把炕门四周的缝隙塞严实,让它慢慢地燃烧。母亲总是把炕烧得热乎乎的,即使外边冰天雪地,寒气袭人,屋子里却温暖如春。尤其是坐在炕上时,那丝丝缕缕的热度慢慢地渗进肌肤,让人感觉到暖意融融的味道。那时,谁家大人小孩看个头疼脑热的小病,请来的赤脚医生临走时丢下一句话,受寒了,趴在热炕上好好暖暖就好了。我们小孩子有时肚子不舒服,母亲和赤脚医生说的一样,让赶紧到炕上趴一会儿,把肚子里的寒气憋出来就好了。土炕饱含了母亲满满的亲情与温暖!
时光荏苒,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旧时代缩影的土炕已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但每当冬天来临之时,故乡温暖的土炕总会潜入我的梦中,我时常怀念土炕上兄弟姊妹翻来滚去嬉笑打闹的情景,怀念母亲盘坐在炕上穿针引线的身影,怀念父亲为我们辅导功课的情景,更想起仍然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
故乡的土炕,是乡土文化的纽带,传递着浓浓的乡土暖意,沉浸着虽然苦涩但却弥足珍贵的人生百味。故乡的土炕,不仅是乡情的承载,更是潜藏在我心底未泯的情愫。
彭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