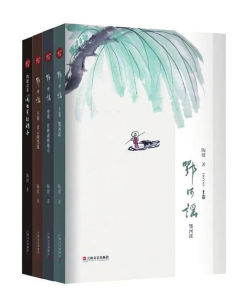乡根与归属的永恒牵挂
——陶健《鄂河谣》的鉴赏观感和思索
《鄂河谣》是陶健先生以细腻的笔触和深情的回忆的一个综合体,洋洋洒洒的几十万文字里诉说和讲述了他与鄂河、他与乡宁、他与乡情之间深厚情感的作品。
阅读鉴赏《鄂河谣》的过程,仿佛就是跟随作家的文字,一同漫步在那条流淌着岁月与乡愁的鄂河畔,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体验作家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掩卷覃思,感悟有五:
一、代入感宛若生活的纽带,把一个个感情节点结绾成深情的回忆
比如鄂河:从一条河流的诉说讲起。文章一开篇便以大量的文笔感念引出了鄂河,这条在山西省西南部默默流淌的小河,虽然不甚宽阔,却在作家心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鄂河从断山岭发源,一路向西,注入黄河,它见证了乡宁的历史变迁,滋养了一方土地,也孕育了乡宁人独特的民俗民风。作家对鄂河的描述,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观的描绘,更是对故乡深情厚谊的抒发。
比如下县村:留在记忆中的温馨家园。下县村,这个位于鄂河岸边的小村庄,是作家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文章通过对下县村地理环境、村民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细致描写,展现了一个充满田园风情和人间烟火气的小村庄。尤其是对姥姥家的描述,那青砖院子、火炕、高窗、狗窝等细节,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温馨而又略带简陋的家中,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亲情的力量。
比如乡宁人:那些纯朴而坚韧的灵魂。陶健先生在文中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乡宁人形象,他们纯朴、善良、坚韧,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无论是挑茅粪的小舅,还是卖菜的下县人,抑或是那些有着各种生活故事的疯人,他们都是乡宁这片土地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让这片土地更加生动、更加有温度。
二、岁月流转的深沉诘问,促成了成长痕迹与文化传承的体悟和反思
《鄂河谣》不仅仅是对故乡的回忆,也是对作家个人成长历程的梳理和反思。从初到乡宁的陌生与不适,到逐渐融入这片土地,再到离开故乡追求自己的梦想,作家经历了从边缘化到归属感的寻找,再到最终的理解与释怀。这些成长中的点点滴滴,都被作家巧妙地融入对故乡的描写之中,让读者在感受乡情的同时,也能体会到成长的艰辛与美好。同时陶健先生在文中还提到了许多与乡宁文化相关的内容,如四月八会、婚丧嫁娶习俗、地方饮食等,这些内容不仅展示了乡宁独特的文化魅力,也引发了作家对文化传承与反思的思考。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让它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是作家留给读者深思的问题。
三、独特视觉里的用心倾诉,深刻地探访了乡愁记忆与人文的呼唤
纵观全书,大家都会发现陶健通过个人化的叙事,将乡愁从抽象的情感升华为具象的文化符号,而且,在其作品里时不时地总会重复着这个绕不过去情结。是的,那就是作家眼里的情结,那就是作家心中的心结,那就是对乡情故土执念里浓浓的“乡愁”,而且集中地体现着几个特点:诸如把乡愁作为生命记忆的载体,作家将鄂河沿岸的琐碎日常(如姥姥家的火炕、村口的槐树)转化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意象,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使乡愁脱离了单纯的怀旧情绪,成为连接个体成长与地域文化的纽带。文中对挑茅粪、卖菜等生活场景的白描,恰恰构成了最鲜活的乡土档案。诸如把乡愁中的辩证思考,不同于传统乡愁书写中对“逝去美好”的单向追忆,作家既呈现了香椿炒鸡蛋的温情,也记录了干枯河床的生态变迁。这种对故乡“既眷恋又审视”的双重视角,使作品具有现代性反思的深度。诸如把乡愁的文化重构价值,通过将民歌、方言等元素融入散文(如《襄河谣》中“喊河”习俗的描写),作家将个人乡愁升华为对晋南文化的抢救性书写。这种“用文学保存文化基因”的实践,超越了私人情感范畴。这样一来陶健的乡愁哲学,就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文化自觉——当我们在水泥森林中吟诵《鄂河谣》时,唤醒的不仅是个人记忆,更是一个民族对精神原乡的永恒守望。
四、延伸“乡宁情结”到“我与故土”,是解读地域文学的核心钥匙
从《鄂河谣》中陶健所关注到的“乡宁情结”到“我与故土”来看,作家的笔触是从三个维度展开这一命题:首先在“我与乡宁”的描述中突出了记忆的地理锚点。陶健文本中的乡宁(如《挑茅粪》中的南坡巷),本质是作家用文字重构的“记忆地图”。这种书写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物理坐标:襄汾方言词“居舍”(房屋)的反复出现,将情感固化在具体空间。另一方面是精神坐标:对“七月十五送面人”等习俗的描写,使地域成为文化认同的仪式场。其次在“我的乡宁”强调了上主体性建构的悖论。作家在宣称故乡故土的同时,也在被故乡所定义,诸如主动塑造:陶健选择记录“打土坯”“漏粉条”等濒危技艺,实质是文化话语权的争夺;诸如被动承载:其散文中的“黄河滩枣树”意象,又反向规训了读者的乡宁想象。再次在“乡宁的我”渲染身份认同的液态化上,最耐人寻味的是陶健作为“襄汾人写乡宁”的跨界视角:比如在地性消解:显现了其文本中“姥姥的布老虎”(襄汾手工艺)与“乡宁油糕”的并置。
五、两地体验的身份互换,构成了新乡愁概念的认同与升华
当陶健记录“倏忽五十年”的生命片段时,大家都能感觉到其文字的挽歌意味,但是有了重建精神原乡的砖石的乡愁回归,则是他带着记忆继续前行的探索底气。特别是从乡宁到襄汾两个地方的异同身份体验上所产生的新乡愁意识,是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将“他乡”转化为“第二故乡”的具体实践。分开来讲能感觉到四个特点:
一是将吕梁山的雄浑与汾水的温润升华为精神符号,山川不仅是物理存在,更成为承载文化认同的“情感等高线”。这种对自然景观的抒情性书写,实质是对工业化进程中失落地景的文学补偿。由此使乡愁的时空重构,进行了地理记忆的审美转化。
二是在《鄂河谣》上卷通过童年记忆(如“杏茶饭”“油粉饭”)与当下感悟的并置,形成时空交错的乡愁图谱,使过往成为抵抗现代性焦虑的精神堡垒。巧妙地把时间维度做成了折叠的叙事。
三是通过微观生活的神圣化对“臊子面配料”“蒸鸡蛋羹火候”等生活细节的极致描摹,将琐碎日常转化为文化仪式,赋予庸常以史诗般的尊严。在味觉记忆的符号系统里将“乡宁虾酱豆腐”“曲沃煿粉”等地方饮食的反复书写,构建起味觉驱动的记忆编码体系,使乡愁获得可咀嚼的物质形态。
四是在《有距离的地方》中“真善美追求”的宣言,将乡愁的现代性困境转化为道德重构的参照系。揭示了新乡愁的本质——既是地理锚点,又是精神游牧者的永恒乡野。这种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在无形间也强化了城乡张力的隐性表达。
这种乡愁书写指向存在主义命题的尝试中,我们尤其可以看得出,当陶健在《腊月集》中描写乡宁年俗时,他既是文化现场的“记录者”,又是被记录对象“改造”的文本产物。这种主客体的永恒博弈,恰恰印证了德里达所言“所有的故乡都是写作的发明”——我们终其一生,都在用文字重建那个永远回不去的地理原乡。
读完《鄂河谣》,我被作家那深沉的乡愁和强烈的归属感所打动。鄂河不仅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作家心中永远的精神家园;乡宁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作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走到哪里,那份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都会如影随形,成为作家心中永远的牵挂。同时,《鄂河谣》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鄂河”,它流淌着我们的记忆、情感和梦想,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鄂河谣》是一篇充满情感与深度的作品,它以鄂河为主线,串联起了作家对故乡、对亲人、对成长的回忆与感悟。阅读全文期间,跟着作家的笔触我们仿佛也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感受到了那份跨越时空的乡愁与归属。
闫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