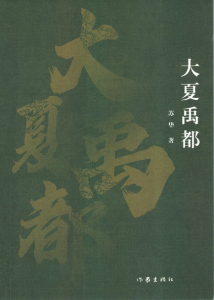对夏都所在的有益探索
——评《大夏禹都》
“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这是周人对大禹的颂歌;“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这是孔子对夏禹的论断。然而,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史书记载又是简而又简,于是造成一方面大禹无人不知,一方面又苦于其都城遍寻不及。于是,夏禹及其国都到底在哪里,便长期处于莫衷一是、反复争辩之中;而寻找夏墟则成为考古和历史学者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
初冬时节,拜读苏华先生的新著《大夏禹都》,由衷感到这是山西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贡献,也是山西学者研究和书写夏文化的可喜收获。
纵观全书,对夏朝国都的材料发现与历史逻辑上的证明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贡献。
一是新材料的运用完善了李济西阴村考古叙事
已经出版的几部《李济传》和为数众多的讲述李济在西阴村考古取得的破天荒的成就叙事,大多依据的是李济的《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结论也惊人一致:由中国人自主进行的第一次现代考古。作者主要利用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博士洪广冀所著《毕士博、李济与“中国人自己领导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中国即田野——毕士博及中国于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中的美国宾州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史密森研究院档案馆、弗利尔艺术馆的档案史料和清华国学院学生戴家祥的回忆,完善了这一著名的考古叙事。其中不乏耐人回味的故事情节,如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特派中国的考古专员毕士博为激发李济的田野考古构想,每逢周一便举行一场午餐会,邀请诸如北京协和医学院体质人类学者史蒂文森,遍游山西西部、美国治外法权委员会的耶卡布斯等人与李济座谈;梁启超在参加清华国学院为从夏县西阴村考古归来的李济、袁复礼举行的茶话会后,秉烛给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的次子梁思永写信,以及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恭喜山西”的贺电,等等,均为笔者目之所及闻所未闻的精彩补述。而对这次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的一个重要历史复原就是西阴村考古是由美国史密森研究院策划并出资,且有毕士博在现场的中美学术团体合作进行的成功范例。
二是利用“二重证据法”对夏都所在进行考辨
关于夏禹的都城所在,有多种说法。有些学者据文献记述和考古发掘推论,认为河南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遗址较有说服力,而支持禹都安邑的似乎既少又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所采信。在历史上曾有过的“禹都安邑说”,在不占主流话语权的学术环境中,如何进行诠释,怎样进行考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令人欣慰的是,作者有意无意地使用了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既利用了新近地下的考古材料,也运用了史书记载的文献材料,将两者相互印证,在多处做出了言之有理、辨之有据的判断和精彩的叙述。如“禹生石纽”,与大禹相关的诸多旧志均沿袭了这一说法。作者先引《四川通志》与此的记载,再用辛亥革命老人于右任和山西籍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卫聚贤亲自到传说发生地汶川刳儿坪实地探访的旧事,证明“禹生石纽”只是一个传说而已。而其传说的发生及其流布,皆因羌人善于治水而来,其主要之法是用“笼石”,故而有“禹生石纽”的传说及其后的地名留存。是传说,还是大禹真的出生在刳儿坪,读后很容易让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该书第七章“大禹以事功摄政”,作者则用康熙年间登封知县张圣诰纂修的《登封县志》所载:“登封,《禹贡》豫州地,唐虞皆然也。古号阳城,禹避舜子于阳城,即此。”反证了三百年前的登封修志的精英已经承认阳城只是禹避商均之地,而不是夏禹的都城。另,史学家、方志学家傅振伦在《文献上的夏都所在》一文中明确指出:“考《汉书·地理志》……阳翟不云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国,可知阳翟是禹的封国而不是禹都。”对于傅先生的这一论断,作者在同一章内也有着很好的遵从。
三是利用方志发掘的史料把汤都、禹都定位在山西
当所有的典籍和史料几乎都被学者用过了的情况下,如何找到新的材料进行历史叙事,不啻在故纸堆里翻找一线希望之光。我注意到,作者是在顾颉刚《研究地方志的计划》的引领下,叩开了地方志这座宝库的大门,并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绩。其具体运用主要体现在以清康熙进士张象蒲的《亳都辨》,乾隆进士安清翰的《成汤古亳实迹说》,光绪年间郭带淮的《禹都安邑考》的考释之文,又结合相关县志中的古迹名胜、人物、碑刻、诗文,予以了翔实的本事抒写。
作者在“引言”中有一段评述史学大家顾颉刚的话:“学历史的人,如果在一篇文章中有所发现或创见,已属不易;在一本著述中有些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新材料、新观点的使用,便呈鹤立鸡群之势;如果能创立自己的一个史学理论和体系及流派,无疑便是天才才会有的事情了。”我想,作者岂止是景仰顾先生的一个人,而且还是按照顾先生的治学方法进行夏禹研究并利用方志状写夏时代的一个有心人。全书八章,新材料、新发现、新识见,章章可见,这种不囿于陈说,用新史料说话的扎实功夫,撑起了该书对于夏文化和禹都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奔腾不息的黄河创造了绵延至今的华夏文明,四千多年来,民族英雄大禹的丰功伟绩已深深镌刻在华夏大地。《礼记》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夏都城市遗址和夏时代的文字没有发现之前,对大禹其人和禹都何在的求索及研究就在路上,苏华先生的《大夏禹都》无疑是这条探索路途中的一个鲜亮路标。
黄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