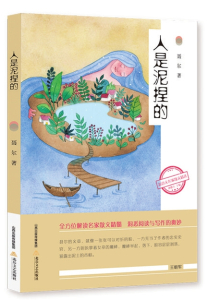聂尔散文里的乡愁
我从聂尔的散文集《人是泥捏的》里摩挲出一种目光,它属于孩童,或者说它被预设为来自孩童。它正奋力穿过小主人的双眼,辨认这陌生而广大的天地。这是一种直视事物的眼光,在它的路径上没有人类经验的背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藤蔓,只有新鲜的、透明的感官,它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世界的图景诚实地映现在它背后那面心灵的镜子上。
因此,它在《王莽岭看雪》一章中看到的就不再是李白杜甫的雪,老舍的雪,普希金帕慕克的雪,也不再是“独钓寒江雪”或雪落人群的喧闹,而是它独自认领的雪。“我看见了光在每一处的变化,风在雪地留下的痕迹,林中细弱的草如何与雪纠缠。”还看见“野鸡脚印。它那清晰的三根指头印下的脚印,形成一条直线,仿佛一行自然的密码,静谧地指向路边深沟。”
很难说这些发现都是拜孩童眼光所赐,但它们会造成一种时间上的错觉,让人以为这就是人类最初看到的事物的模样,最“简单”,最直接,也最真实。所以当我们跟随作者发现光之于雪的秘密时,同样为之惊喜。因为我们信了。而这信,并非源自已知,而是源自未知,或者说是将已知转换为未知。此时,作者已悄然将我们的目光滑动到历史开始的位置,他要带领读者重新勘探和编纂这个自以为无比熟稔的世界。
这多有趣啊,因为我们的好奇心有了满足的可能。谁都知道,未知的世界里遍布“奇遇”,既然王莽岭的高处有,生活的低处也应不遑多让。这不,《短暂的猫咪》和《我家里的空气》便将“奇遇”落实到了匍匐在地面之上的人间。
猫咪是带着庄严的使命来到作者家的,这使命很实用,因此也很短暂,就是抓老鼠,除此之外,在作者眼里猫并无他用。可猫咪并没有沿着人类规划的蓝图行事,非但抓没抓着老鼠成为一个谜,还留下了斑斑“劣迹”。
窗台以及其外别样浓重的夜色,茶几下搁板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隐秘通道,地板上的每一条砖缝直至其每一寸光洁的空无之处,还有我那久已无人光顾的大写字台荒凉的表面,以及我家所有可能的角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
当然,省略号里还藏匿着一条猫咪极不得体的罪状,那就是在妻子的被窝里睡了一整天。这是猫咪诸多“劣迹”的延伸,也是它最终被决定赶出家门的直接诱因。在此之前,猫咪就像一个傲慢的女王,在它的领地上巡游,尽管该领地狭小而局促,但它总能在复杂的局面里寻找到一条鲜为人知的通道。对,就是“鲜为人知”,当作者和他的同类还在汲汲于生活的功用时,猫咪却以它短暂而偏僻的行程揭开了这个世界的内在奥秘。事物由此脱离了“合法”的认识轨道,重新在我们生活的平面上耸动、拱起,直至“呈现出如同山峰一般的高度”。
我们在,就必须出具一份在的证明。在《我家的空气》里,聂尔就出具了一份强有力的证明。他以普鲁斯特式的耐心和敏感,精心搜集了各种身份的空气,并为空气钻探出味道。当然,聂尔知道这事儿唠起来没完,所以他明智地选择适可而止,味道学研究的方向也迅速转向了自身,转向了“我家”。
“我家的空气”是怎样的呢?在妻子眼里,是“万千飘荡的尘埃”;在女儿劈波斩浪的身姿下,是摄于威严的“动荡”;到了作者的鼻端,则是一寸一寸的书的味道。我就知道作者会将空气最终收拢到书里。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宿命,不谈书,你难道让他谈股票不成?
但我关注的不是这些,我关注的是语言本身的幽默和躲闪在幽默之间的智慧。何以幽默?在聂尔,则是汪洋恣肆的想象,还有对自身经验的高度执着。你看,诸种空气在他心灵感官的扫描之下,显影出一帧帧风景的奇观。而在这些奇观中,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以及人的所有感觉,都经由联想和想象的加工、转换、淬炼,释放出精神的“味道”。这些精神味道长久地潜伏在时间深处,等待想象的密钥将其激活。聂尔直觉地找到了密钥,也就唤醒和穿越了他的“普鲁斯特时刻”——通过嗅觉瞬间开启记忆中某个时刻的特定感受。
举证并不困难,例如“戳指可破”的如绸缎裹着一具华丽胴体的《追忆似水年华》,例如“阴暗潮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例如可以把人变作幸福的蚯蚓的浑身“土味”的卡夫卡。就算离开了书和书的作者,聂尔也能在事物之间建立惊险的、偏远的联系。
写农家空气的味道就是一例。嗅觉上的“稍显污浊”,浅浅的、淡淡的,给人以心理时间的“慢”,甚至这慢还要“慢过时间许多倍”,在视觉上则体现为“在一个深底缓缓地流淌着”。继而通过“积聚”委身于现实的厚墙。现实是什么?现实自然是浓郁的乡愁。但因了感官的有效接通,这乡愁就不再是一种形而上的观念,而是味觉接收到视觉信号后的创造性成像:豆腐渣。“豆腐渣”和乡愁,这两种分别处于物质与精神两端的事物,围绕“童年”记忆达成了一致。
——我断言,幽默就在这“豆腐渣”的体内。如果你有足够的乡村生活经验,乃至你的童年也在乡村度过,你定会对此会心一笑。豆腐渣是乡村生活的常见物;论资历,完全承担得起“数百年”的时间长度;它身上散发出的味道也的确给人以浅浅的污浊之感;而它细碎如蚁的颗粒状,不正像童年记忆的残片吗?至于豆腐渣这种并“不体面”的乡村食材还给作者留下过什么其他印象,我们不得而知。但当你隔开岁月的距离,重新把目光投向农家时,“豆腐渣似的乡愁”很可能让你的鼻腔里涌动着放纵与怜悯、嘲谑和忧伤的复杂感情。
这便是乡愁,它无限小,又无限大。这也是散文的基本伦理,它不一定要做“大事”,讲“大道”,但它要体验并肯定“自由”,在意义世界的海洋里享受探险的乐趣。
这一点聂尔比谁都清醒,所以他在文章的末端行使了彻底的“自由”:“沉默”或“沉默之味”。他解释说:“我要我家的空气只充溢着从未有人描述过的空无之味。”既是空无,本无色无味无形无声,但聂尔还是忍不住在想象中构筑了它的形体(默之丘山)、声音(音乐的声响)和气味(天堂禁果一般的异香)。当然还有色彩,那是吞噬整个世界的纯然的黑。在此,空间的几何学和时间的心理学赋予了“沉默之味”以终极的形象和品质。聂尔也得以雄辩地确认了自己的在。没错,他在,他才能做出选择和行动,他才能在“书写”的行动中“啃啮”出一片智慧的天地。
“真理之有趣并不亚于真理之严肃。”由是观,然也。
所以好的散文会生成一个开放的对话空间,而“我”则小心翼翼地发出声音,接纳来自各个方向的责难、非议,从中求证“我的”信与不信,并由此出发,赶赴新的未知疆域。
王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