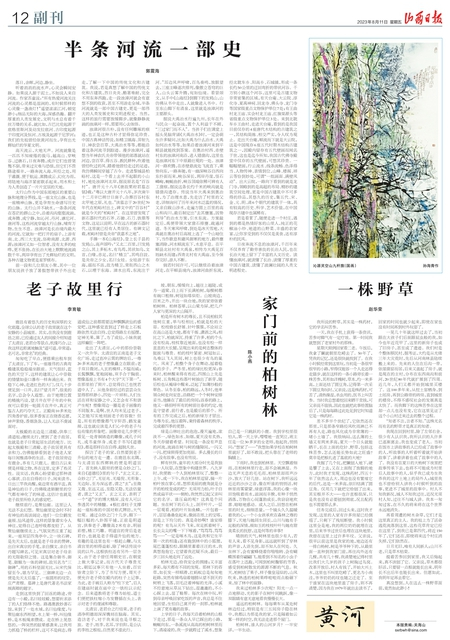一株野草
我所说的野草,其实是一株药材,它的学名叫苦参。
一天,我在手机上获得一条资讯,苦参对脚气有一定疗效。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老家村外的那株。
星期天照例回家看二老。午饭后,我拿了镢就朝里圪崂去了。50年了,凭我的记忆,还是很快就找到了。在我小时候经常到这里玩,当初是一条很窄很窄的小路,窄得仅能容一个人走还得走猫步,就在这样的一条小路旁长着一株苦参,其形如洋槐树,草本,约一米多高,上面还结了圆豆角,记得第一次采下圆豆角玩时,父亲说,这是株药材,可苦了,清热燥湿,杀虫用的,医书上叫苦参。当时我总想着挖回来晒干卖钱,可父亲说不值钱,因此也就把此事给置脑后了,只是每每路过此处见到它时知道它是一株药材。
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它依然还在那里,只是那条窄路经风吹雨淋已不再有人走,路也风化成为非常薄的一堵小土墙了。我很纳闷,这么薄的土墙又有两米多高,夏天一个日头就能晒干,长在上面的圪针、野草,包括这株苦参,怎么还能长势如此之旺盛?莫非是把根扎进了基底的大地?
我掘了几个坑,把镢刨入地下,硬是攀了上去,又在上面削了放脚的地方,此时我才发现,这株药材,四五十年了依然这么大,周边也没有繁殖它的后代,还是一米多高,依旧结满了圆豆角。仅用几下就把它给刨了出来,其实根并不大——也许直根很深,只是我也没有必要刨到彻底,况且配药也不需要那么多。
任务完成后,回过头来,这时我才发现,这里的人家有许多房屋已经倒塌了,只剩下了残垣断壁。我小时候这里全是地,我的两位奶奶就埋在这里,后来爷爷过世后也埋在这块地里,我曾在这里上过许多年坟。父亲说,很早以前这里是我家的地,地边还有一排白杨树,树是爷爷种下的,从最里面一直种到我家门前,再往沟外还有几棵,共有几十棵,我清楚地记得村里比我们大几岁的孩子上树掏过鸟窝。改革开放后,村人有钱了,开始大兴土木,这里也不叫里圪崂了,更名为小南洼,爷爷奶奶的坟也随之迁走了。至于谁家在这块地里盖了房子,则不再清楚,因为我在1979年就出去读书了,回家的时间也就少起来,即使在家也没有时间再到村外玩耍了。
一晃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当初跟在大孩子们后面跟屁虫般的我,如今也年近花甲了,这里的新房子也成了旧房子,甚至成了遗迹。我们村是个整体移民村,据考证,大约是从光绪三年大灾荒时,先后从河南林县陆续搬上来的。先来的人住在后沟一带,依崖凿窑而居,后来又盖起了房子,就是现在的主村,分布在东西南沟和前河,20世纪80年代就扩展到了四周。近几年,人们又都开始到城里买楼了。这100多年来,从挖土窑栖身,到土坯房,再到公路旁的砖房,直到城里的楼房,不得不感叹社会的发展真是太快了。而我脚下的这株苦参在这里却一点儿也没有变,它在这里见证了这个小山村迁来迁去的整个过程。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株无名而有名的野草才是真正的知者。
我现在回到村里,除了左邻右舍,很少有人认识我,我所认识的人许多已逐渐离去,我也变成了老人。当初在饭市上讲故事的人已经成了故事中的人,听故事的人听着听着就开始讲故事了,讲着讲着也成了故事中的人了。我没有在夏日的大杨树下夜里把故事传承下去,也将不可能成为村里后人故事中的人,似乎我已成为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上的局外人;城里我也不曾给别人讲我小时候听到的故事,更进不了城里的故事中。村人不知我新况,城人不知我过往,近况无须村人知,过往不与城人讲。我本一匆匆过客,在不久的将来将在这个世界永远地消失。
再看周遭的树木杂草,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我的祖上为了活命逃荒流落到这里,这些花草肯定已经在这里了,到我已是第四代,将近150年了,它们还在,即使将来这个村庄消失掉,它们依然在。
日月无旧,唯有人间新人;山川不老,只是草木枯荣。
提着苦参回到家里,我又后悔起来,真不该刨了它。父亲说,草木都很好活,只要留一点根就能长出来,明年长不出后年也能长出来。但愿如此。我明年定再去看它。
真没想到,人在这么一株野草面前,竟然如此渺小!
赵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