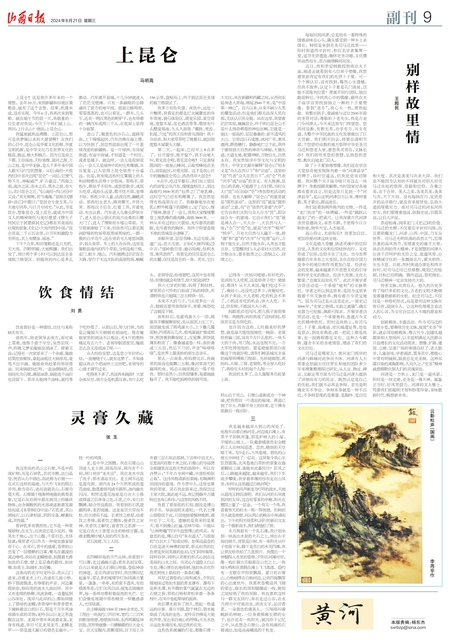饮食情结
饮食喜好是一种情结,往往与某些缺失有关。
前些年,陪老领导去南方,面对桌上菜肴,他筷子悬于半空,突然长叹一声,昨晚又梦见俺娘没胡油了。接着又说: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亲戚,俺娘切菜挖面做饭,拿起油瓶往大锅里甩,竟甩不出半滴。俺娘命我赶紧向邻居借油。回来锅底快红呀,一盅油倒锅里,顷刻间化为白烟,满屋油香,锅底连个油印也没留下。那年头能闻个油味,就约等于吃炒菜了。从那以后,努力打拼,为的是让俺娘天天顿顿有胡油吃。现在俺娘家里的胡油不以瓶论,光5斤的塑料桶足有五六个。老领导眼望虚空,俺娘怎么会又没胡油了呢……
众人纷纷安慰,这是您少年时的心结,一直缠绕于心,就有这梦了。不知谁提议再点个胡油炒土豆丝吧,老领导的心情才调节过来。
吃得差不多了,我说再来碗面!大家全体反对,南方全是机器压面,有什么吃头。老领导说,给他要吧,这其中也有情结,有情结就会有情节,给大家说说吧!
我六七岁的时候,妈得了肺结核,家里那点可怜的白面成了妈的特供,所谓特供也只能隔三岔五特供一回。
本来不大的勺子,勺头里多出一点点,姥娘还要用食指抹平,省着,唯恐吃了这顿没下顿。
面和好后,也就鸡蛋大小一团,姥娘双手横握擀面杖,先从面团上压三下,面团就变成了煎鸡蛋大小,上下撒几撮面粉,四周再压几次,煎鸡蛋就扩展成煎饼,煎饼裹到擀面杖上,反复擀,煎饼就薄如粉皮了。像叠铺盖卷一样,面折叠成三五层,然后下刀切,声音“咯噔咯噔”,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原生态音乐。
那么一点面条,给妈捞完后,我碗里的面汤也能飘三五根,像河里游弋的漏网的鱼。妈总从碗里挑出一筷子给我。那时虽然小,但我很懂事,抱着碗就躲开了。我不能吃妈特供的病号饭。
记得有一次妈问姥娘:有好吃的,是该给大人吃呢,还是给孩子吃?姥娘说,都该!从大人来说,俺们吃过不少了,俺娃小,还没吃过多少,该俺娃吃。从孩子来说,大人老啦,吃的机会不多了,小的还有吃的机会,该大人吃。不过,你有病,不能说大人小孩。
妈眼里泪花闪闪,那几筷子面很难下咽。我晓得,妈怕我成了没妈的娃,那面其实是为我吃的。
也许因为这些,儿时最美好的梦想,就是每天能饱饱地吃一碗面。老舅给我谝三国,说有个左什么慈的,一块不大的干肉,用刀削,永远也削不完,一万大军吃得饱饱的。要是姥娘那团白面像这干肉就好啦,请我们崞县城庆丰泉的海厚师傅做刀削面。先给姥娘削,再给妈、大舅、三舅、老舅削,等全家人吃好了,再给庄头村的每个人削……
我说的太多了,众人催服务员赶紧上面。
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