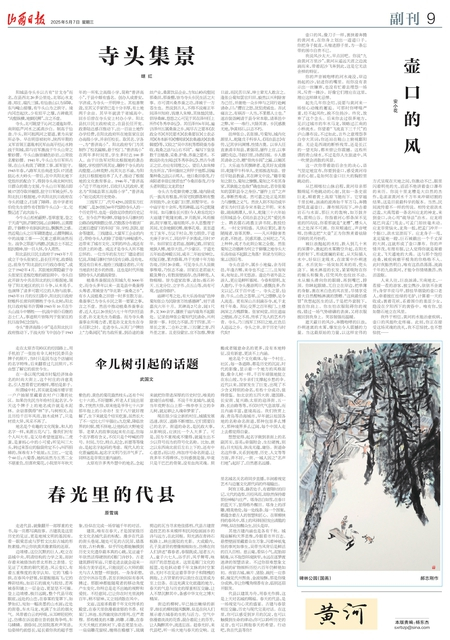寺头集景
阳城县寺头乡以古有“甘戈寺”而名,在县西北20多公里处,北邻沁水龙港、郑庄、端氏三镇,有仙翁山以为屏障,东与崦山接壤,有牛头山为之拱守。境内冈峦起伏,少有坦平之壤,古碑载其“沟壑纵横,地僻民稀”,言之不虚。
寺头,北可眺望于沁河之逶迤如带,南则临芦河水之溪清沙白。制高于仙翁、牛头,则可扼两河之要道,素为兵家所必争。早在明崇祯初年,陕西早期的义军首领王嘉胤率民军由高平经沁水转战于阳城,即与官军激战于牛头山背之紫砂腰。牛头山脉皆赭色砂岩,山背故名紫砂腰。1941年,牛头山为日军所占领,在山头构筑了碉堡工事,派军驻守。1943年春,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17团进驻沁水大岭头一带后,在中共阳北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得到寺头南北树村抗日群众的鼎力支援,牛头山日军据点即被17团夺取并摧毁,驻守日军被全歼,为阳北抗日根据地,中共阳北抗日政府在寺头的建立,扫清了障碍。邑中学者刘伯伦先生曾作有《智取牛头山》一文,完整记述了此次战斗。
今牛头山松柏蔽野,苍翠葱茏,登之于天清气朗,四顾空阔,山回峰转,云蒸霞蔚,于静默中有跃跃欲仙,飘飘然之感。然近观山头之日军碉堡遗址,山腰荆棘丛中的战壕工事……沉重之感则油然而生。战争之罪恶与残酷,民族志士不屈之抵抗精神,皆一目入怀,令人肃然。
阳北县抗日民主政府于1943年7月成立于寺头张家庄,县长任开宪,政委陆达,前身为“阳北县抗日行政办事处”,成立于1942年4月。其驻地初期隐蔽于寺头张家庄老板圪堆的破窑洞中。寺头自此开辟为中共在阳北的抗日根据地,领导了阳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从未易手。也演绎了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与故事。1943年11月的反扫荡中,阳北抗日政府财粮科长席向明牺牲于寺头北树;阳北抗日政府秘书许霄峰1943年10月在牛头山战斗中牺牲……抗战中前仆后继的志士仁人,事迹照片皆陈列于张家庄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内。
寺头“普济高级小学”是在阳北抗日政府推动下,于战火纷飞中创办于1943年的一所私立高级小学,简称“普济高小”,于县中颇有盛名。创办人成普安,字济成,为寺头一开明绅士。其祖善聚敛,至其父手家资已是十分丰厚,有土地两千余亩。其早年就读于省城高中。回乡后曾在寺头安上村办小学。阳北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在县长任开宪、政委陆达感召推动下,出一百亩土地作办学经费,在阳北政府所在地张家庄创办高级小学,并亲任校长。取其名、字各一,为“普济高小”。阳北政府专门为其制作了校名匾额,悬于校门。“普济高小”在两年多时间里,学生多时达100多人。由于日伪军对阳北根据地的袭击骚扰,学校曾四易其址,辗转于寺头的沟沟壑壑,山林荒野,而其矢志不渝,为阳北抗日根据地培养了人才,推动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1946年,“普济高小”迁于芹池刘村,后收归人民政府,更名为“阳城县第五高级小学”。“普济高小”始完成其历史使命。
三线军工厂,代号4291,国营东方红机械厂,是20世纪60年代留给寺头人的一个历史符号,也是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至今在芦苇河畔,穿越寺头马寨村的公路沿线两侧数公里,仍散落分布着该厂迁离后遗留下的车间厂房、学校、医院、宿舍等建筑。三线建设,大量军工企业的内迁,带给寺头人的除了崇敬与神秘感外,还带来了城市文化、文明的冲击,或还有经济上的补遗。或这才是寺头人所不能忘怀的。一位当年的东方红厂建设者回忆说,阳城马寨村当时没有公路,没有电,更没有自来水,能给三线建设者的,只有当地农村老乡的热情。这也是时代所能留给寺头人的最高荣誉。
植桑养蚕据说在阳城久有3000年史,而寺头多年以来一直是县中桑蚕得头筹者,常被誉为“华北第一蚕桑之乡”,有乡人说植桑之田曾一时多至数万亩。桑蚕事已为寺头乡民之第一要紧之事,言之不虚。然邑中推动植桑养蚕事业者,近人尤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任县长者,孙文龙先生为最盛。而为寺头桑蚕事业所竭力者,更是孙文龙先生在寺头任职之时。走进寺头,从其门户牌坊上“力桑润民”的为政所重,到沿途的蚕丝产业,桑葚饮品企业,方知山岭沟壑间那桑田,那蚕棚,皆为寺头乡民生活之大事。亦可谓兴桑养蚕之功,泽被于一方苍生也。然说到古人,不得不说雍正年间泽州知府,钱塘人朱樟,其体恤民情,倡导桑麻,悠悠之心可见于其在泽州任上所作《冬秀亭杂记》。其任泽州6年间,遍访泽州五属桑蚕之乡,阅尽古之要本《农政全书》《齐民要术》《农桑要旨》《士农必用》《务本新书》《博闻录》《农桑通诀》《农桑辑要》等,又较之“吴中苏杭等郡倚蚕为春收,栽桑之法与山右不同”。编写下皇皇数千言植桑、采桑、护桑、养蚕之要术。不敢说孙先生阅过《冬秀亭杂记》,然古今清正之官,亦应有同理之心。望后人如朱樟先生所言,“泽州蚕丝之利甲于他郡,因编集种桑之法以示邦人。他日桑田春茂,行南陌者幸毋忘使君也!”今桑田春茂,行寺头者则莫忘文龙君也!
寺头古为荒僻贫瘠之壤,境内除成氏一族浅有根基,所居宅院群落稍有整齐别致外,余无豪门巨贾,别墅华宅。乡中庙宇有十余所,考其碑碣,远不过乾隆年间。如马寨东长兴里(今人称东圪坨)大庙建于乾隆初载,岁月既深,风雨摧剥,院宇靡芜,墙垣败坏,乡人思整理于其间,无奈地僻民稀,做事孔艰。直至道光丁亥年,方议于村众,努力捐资,于道光庚子岁兴工,同治甲子岁落成,历时37年。如田家庄老君庙,据碑记载,田家庄地狭人稀,地非大邑,户少豪宗。于道光五年始造神殿五间,咸丰二年始安神位,绍复后继,累次修葺,终于光绪十年方始告竣,历时20余载。可见寺头古人虽做事维艰,乃恒志不渝。田家庄老君庙大殿及舞台,有数面壁画存,色泽鲜亮,人物栩栩。皆为道家故事,诸如:炼石补天、五龙分位、立字书、点五山等,尚有可观,也亟待修护。
庙碑可考之处,有大乐汤帝庙“邑绅菊知张公为民除害万姓感德碑”,刻于清嘉庆六年十月。其碑高2尺余,阔1尺多,文300余字,镶嵌于庙内墙角不起眼处。记录邑绅张公菊知代民请命,兴利除害一事。时民力不堪,苦于四害,其一里长之害,二仓补之害,三拉骡之害,四外差之害。且吏役蒙官,官不加察,弊害日滋,而民苦日深,绅士辈无人敢言之。逢张公菊知罢官归田,毅然以兴利除害为己任,并谢绝一众乡绅与之同行赴阙请命,曰:“撄官之怒,犹犯虎威也。吾试痛言之,有祸吾一人当,不累都人士也。”遂治装诣阙请于县令宋本敬,请革邑中之弊,宋一一准行,大除其害。乡民感激无地,争谋刻石,以志不朽。
邑绅张公,名张锦,号菊知,城内化源里人,乾隆戊子科举人。《同治县志》有传,记其学问渊博,性情古奥。以举人任直隶清丰知县,素强项,屡忤上官,以事谪贬戍边,寻赦归里,诗酒自娱。乡人德其请命之功,赠“骨肉乡闾”之匾,以额其门。大乐庙为其撰碑者,是其好友成锡田,乾隆甲午科举人,吏部拣选知县。曾任平陆县教谕,其在碑文中说,“籍非菊知之胆力,菊知之慷慨,菊知之不有其身家,其孰能之也哉!”确也如此,若非张菊知的罢职县令之身份,“屡忤上官”之声名,事断然难成。然可嘉之处正是其胆力与慷慨之义气。然世人则不知功成半者实为时任县令宋本敬之开明。宋本敬,湖南湘潭人,举人,乾隆三十六年始任阳城县令。《同治县志》记其“爱民养士。聘名儒石鸿翥主讲书院,教授经术。一时文学较盛。凡供应累民,著为陋规者,皆革其弊。……凡兴利除害类此者,不胜述。民感其德,立祠祀之。”凡上种种,或才为此则公案之全貌。然张菊知之功德碑为何立于僻壤之地寺头大乐汤帝庙不起眼之角落?则录为另则公案,以图后考。
寺头在县中,属乡小地偏,余为同邑,年逢古稀,来寺也不过二三,且匆匆来,匆匆去,并无悠游。遑论外省外县之游人,更应是鲜听寡闻。今春和景明,友人邀约,于寺头漫游两日,感慨良多,作文以记,仅于百中述一。寺头之景,仙翁、牛头,山色之苍翠,云气之缥缈,足令人流连。更有深山古刹滴谷寺,虬干龙枝千年桑。阳沁交界之百年税门,土楼涧深之古槐群集。张家祠堂,田庄道庙之壁画,存之不易,传承了先人的艺术丹青。寺头,乃三线军工怀旧之地,红色后人追远之乡。寺头之幸,幸于历史与时代矣!
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