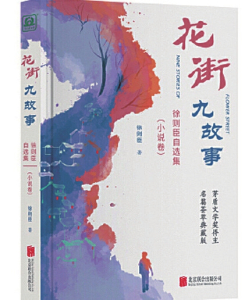花街的故事
——读徐则臣《花街九故事》
花街故事知多少?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徐则臣在《北上》《耶路撒冷》《一意孤行》等多部作品中提到过花街,并讲述了许多关于“花街”的故事。
《花街九故事》更是以花街为背景,捕捉了边缘人群生活中的日常细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花街上人们的坚韧与执着。这部作品是作者对故乡的深情回望,更是对社会大众的深刻洞察。他所营造的“花街”,用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浓情的文字,赋予花街特殊的气质,氤氲着一种气息,甚至灵魂,使读者们深信花街是有深厚文化积淀的。
花街,是徐则臣的故乡。他曾说:“早晚以花街为名出一本主题小说集。”《花街九故事》就是他的兑现之作。花街,亦是徐则臣构建的纸上故乡。他说:“在一个小地方,困守于一个地方的人,他们对世界有着巨大的想象,他们会争取各种机会,沿着河流往世界走,所以这里面的人,既有传统的、本分的,也有不安分的、开拓进取的;既有凡夫俗子的日常的烟火生活,也有他们传奇的、另类的那样一些经验。这个世界有多广大,花街就会有多漫长;这个世界有多复杂,花街就会有多丰富。”花街,在徐则臣笔下,有深度、有宽度,也有高度。
九个故事,无论是环境描写还是人物刻画,都各具特色、栩栩如生。如清晨湿漉的青石板铺成的道路、临街面对面的灰旧小院、街边大大小小的木板房店铺、运河边春日盛开的槐花、夜晚房檐下挂着的红灯笼等,深深打动了我的好奇心,很想立刻亲临这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
九个故事,有的真实发生在花街上,如《花街》里大榆树下修鞋的老默与开豆腐脑店的蓝麻子一家之间的故事;《人间烟火》里的苏绣和郑启良;《失声》里原本幸福后来为了生活被迫“挂灯笼”的姚丹;《大水》里靠着运河打捞为生的沉禾与屠户年七的故事;《苍声》里被抱养的大米与养父何老头;《镜子与刀》里爱打老婆的老罗;《伞兵与卖油郎》里范小兵家的故事。也有的是作者臆想的,如《如果大雪封门》和《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他说:“故事跟花街有关即可,哪怕人物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他思在花街、念在花街、根在花街,为什么不能算作花街故事呢?”
九个故事里,有一点深触我心灵的,是对女性角色的描述。“女人,像一棵棵开花的树,表面漂亮鲜活易摧残,内里一直坚韧不屈,她们求生的根深深扎进土壤里,虽遭受许多磨难和不公,但她们一直顽强地开着花。”
九个故事中,那些不会言语的灰砖青瓦、街道码头,都蕴藏着丰富的故事,因此,每天都会有许多外地读者来到淮安,寻找徐则臣笔下的“花街”。渐渐地,花街成为徐则臣文学创作的根据地。他说:“一写东西,我就必须把故事的发生地搬到这里来,才觉得得心应手。”
读完《花街九故事》后,我越发觉得,花街宛如一坛醇香老酒,越品越香飘浓郁。历尽岁月沧桑的花街,由原来三四里的长街,变成了如今二三百米的短街,长度虽变短了,但它的历史厚度和文化底蕴依旧在。如长篇弹词《笔生花》的作者邱心如,就是从花街走出去的文人,著名历史学家郑振铎对《笔生花》的评论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作家申海琴的《花街》:“花街的来历……我倒觉得是因为邱心如似花一般的美貌,和她创作的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笔生花》而得名的。因为在我看来,邱心如就是花街的形象大使,成了花街文化底蕴和气质风韵的代表。”杨溢的《淮安花街》:“无论早晚,饮食摊点星罗棋布,花街的小吃早在乾隆年间品种就达百余种,虽历经百年沧桑,小吃品种仍斗艳争奇:文楼汤包、菜蒸包、油煎包、炕饺、牛肉馄饨、肉丝面、黄桥烧饼、牛舌烧饼、烤牌、油端子、浦楼茶馓、麻花、绿豆圆、薄脆、糖粥、蒸糕、糯米甜藕……这里的美食,多到令人眼花缭乱,嘴吃不过来。”何永年在《花街旧忆》中说花街店铺琳琅满目,包括朱桂记印刷店、蔡姓白铁店、粉团店、许源和丝线店、王元记蜡烛店等。
如今的花街,店铺依旧琳琅满目,连接的运河边成了美食街,晚上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石码头、青石板路上、运河边,人们穿梭其中,忆着花街的老故事,寻着花街的新故事……
金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