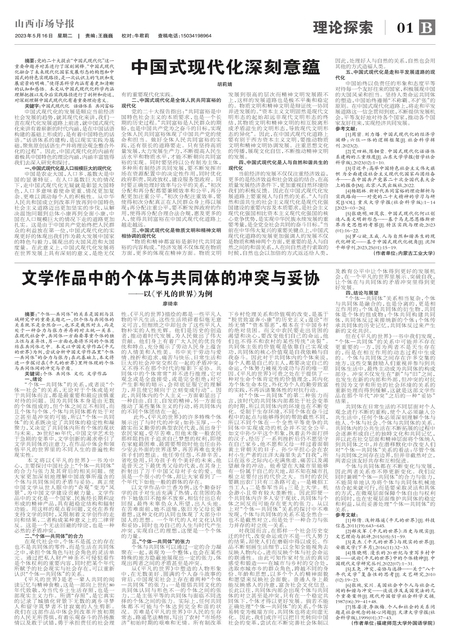文学作品中的个体与共同体的冲突与妥协
——以《平凡的世界》为例
摘要:“个体—共同体”的关系是国别与区域研究中的重要主题之一,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既不是全然合一,也不是截然对立,而是处于一种合力与张力并存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共同体一方面要尊重个体的独立性与差异性,另一方面也要将不同的个体团结在共同体之中。本文以中国文学作品《平凡的世界》为例,尝试分析中国文学作品里“个体—共同体”的合力与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在《平凡的世界》里所体现的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冲突与矛盾。
关键词:个体 共同体 文化 文学作品
一、绪论
“个体—共同体”的关系,或者说“个体—社会”的关系,无论对于个体或是对于共同体而言,都是最重要和最应该慎重对待的问题。因为共同体本身是由无数的个体组成的,但个体之间互不相同,而且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共同体都有处于对立甚至是冲突的可能,所以“个体—共同体”的关系既决定了共同体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又决定了共同体内所有个体的现状与未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处于急剧的变革中,文学创新的渴求牵引了文学共同体的注意力,在作品中体会和领悟平凡的世界里的不同人生的普遍性和现实性。
本文将以《平凡的世界》一书为中心,主要探讨中国社会上“个体—共同体”的合力与张力及其背后的相关问题。使大家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故事所蕴含的个体与共同体间的矛盾与妥协。真正使中国文学从世人眼中的“奇观”变为“风景”,为中国文学建设贡献力量。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经长期积淀形成的精神产品,具有超稳定结构和辐射功能。用这样的观点看问题,文化在养育支持文学的同时,又限制着文学创作的走向和结果,二者构成某种意义上的二律背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也是一种必然的矛盾冲突。
二、“个体—共同体”的合力
在现代社会中,个体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共同体的零件,而是生活在共同体之中,承担个体角色与社会角色的灵活单元。通过把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看作是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同时把某个年代所赋予的社会现实与社会存在,可以重新认识“个体—共同体”的关系。
《平凡的世界》是老一辈人共同的阅读记忆与精神食粮,这是一部向上世纪80年代致敬,为当代乡土生活存照,也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所谓“存照”,是它真实的记录了城镇化背景下无数的离乡寻梦人和留守筑梦者不甘寂寞的人生剪影。我们在这部作品中体会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民无所畏惧,有着乐观奋斗的昂扬激情以及敢于试错,勇于承担责任的社会理性。《平凡的世界》描绘的都是一些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这些生活琐碎看似毫无意义可言,但细琐之中却包含了这些平凡人物朴实的人性光辉。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着时代发展,为人民做出了伟大贡献。他们身上有着广大人民的优良传统和特点,充分揭示了劳动人民身上蕴含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书中关于劳动与爱情、挫折和追求、痛苦与快乐、日常生活和巨大的社会冲突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冲突,又不得不在那个时代的缩影下妥协。共同体中的个体常常“并不进行推理,它对观念或是全盘接受,或是完全拒绝;对它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它的理解力,并且使它倾向于立刻变成行动”。因此,共同体内的个人主义一方面彰显出了一种自由、自主、自发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某些集体主义的行动,将共同体内的不同个体团结在一起。
此外,《平凡的世界》的许多特殊个体展示出了与时代的冲突:如孙玉厚,一个踏实而又勤劳的典型农民代表,虽出身于农民家庭,受尽苦难,但他未像一般农民那样阻挡孩子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即使在家庭最困难、最需要帮助时他也任由孙少安去外面的世界逐梦,再苦再难也支持孩子们的想法。他任劳任怨,不辞辛苦,省吃俭用,只为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他是普天之下最优秀父母的代表,在其身上折射出了万千中国父母对子女的爱。他虽是一个很小的个体,却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年代下如他一般的群体的存在。
以文学作品中兰香为例,这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在贫困的条件下她依旧不抛弃不放弃,相信付出总有回报,最终未辜负众人所望,出人头地。在苦难面前,她不退缩,依旧为父母长辈着想,这种文化的认同也体现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思想。一个年代的人对文化认同和妥协,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与时代产生冲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便是一个个体的力量。
三、“个体—共同体”的张力
个体与共同体可以通过一定的合力凝聚在一起,表现为一个整体;也会在某些特殊的地方隐蔽地展现出一定的张力,体现出两者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冲突。
从《平凡的世界》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在无数美好、圆满的个人奋斗故事的背后,中国现实社会上存在着两种“个体—共同体”的张力:一是提倡共同文化的共同体认同与形色不一的个体之间的张力,二是主张平等的共同体与面临不同选择的个体之间的张力。实际上,任何共同体都不可能与个体达到完全和谐的状况。苦难是《平凡的世界》中人民的生存常态,路遥笔法精细,写出了农村“市场经济”初始时期的艰难和无情。所有制改革下乡村伦理关系和价值观的改变,是基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历史正义;遑论“市场无情”“资本罪恶”,根本在于中国乡村的绝对贫困。而文中农民要走出贫困的渴望和决心,要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也不得不和农村的某些传统“决裂”。共同体主张的价值观是依靠自己实现成功,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是自我依赖与自我奋斗。因此对于共同体内的个体来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都要决定自己的命运,个体努力被视为成功与否的唯一原因。《平凡的世界》可贵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对生命个体肯定性的价值理念,其内化为个体生命本位,外化为个人的勤劳致富的实践,不再诉诸集体性的对抗行动。
对“个体—共同体”的第二种张力而言,该时代的共同体内部都处于社会变革的时期,所以共同体内的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受制于生存环境,不同个体在奋斗过程中的起点与能够得到的帮助截然不同,所以不同个体在一个全然平等竞争的共同体中实现成功的机会并不完全公平。如文中孙少平这个形象,执着去外面打拼的汉子,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仍不愿坚守在自己家乡,他不愿和父母一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孙少平担心会在农村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里失去“自我”,所以在返乡之际内心充满焦虑、痛苦以及渴望献身的冲动。他希望在大城市里能够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天地,却不知在城市扎根立足要付出的代价之大。当时的农民要跳出农门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被招工当工人;二是参军当兵;三是上大学。机会渺小且带有较大垄断性。因此即便一个共同体内许多人安于现状,共同体与个体之间反而可能存在更大的张力。从以上对“个体—共同体”关系的探讨中不难发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不是全然合一也不是截然对立,而是处于一种合力与张力并存的对立统一关系。
对我国而言,在那样一个社会历史变迁的时代,改变命运或许不是一代人努力的结果,却使人们在磨砺中得以成长。作品不断刻画生活细节,以全知全能视角去反映人物内心,进而反映个体与社会命运的联通性。由此可知作家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和锻造——在城市与乡村的交合处,选取亦城亦乡的群众角色,跨越不同的身份、年龄和思想,以多个个人的精神面貌和愿望来反映社会面貌。普通人身上最能反映感人的诗意,富含社会文化信息。长此以往,共同体内部会出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甚至是冲突,只有在一个稳定共同体下,个体才得以更好发展。倘若不能正确处理“个体—共同体”的关系,个体容易转变为极端方向,共同体也将走向虚无化。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目光转向中国社会的变革,尝试在不断完善社会体制以及教育公平中让个体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在一个平凡的世界里展示、突破自我,让个体在与共同体的矛盾冲突里得到更好发展。
四、结论与展望
“个体—共同体”关系相当复杂,个体与共同体是融合的,也是分离的,更是相互作用的:个体是共同体的衍生物,共同体是个体的组成物;个体共同构建共同体,共同体反过来接纳新的个体;个体传承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共同体反过来产生新的文化共识。
但在《平凡的世界》一书中我们发现,“个体—共同体”的关系中可能并不存在更重要的一方,因为两者不是天生存在的,而是在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生成的。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存在许多交集的地方,这些交集鼓励人们重视并参与到共同体生活中,最终主动成为共同体的构成部分。冲突不仅发生在“新”与“旧”之间,也发生在新的内部和外部,但冲突的对抗性因为文学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关系的重新处理而得到缓解,这就是这部文学作品在那个年代“冲突”之后的一种“妥协”结果。
共同体在日常生活的不同层面对个人观念进行不断的重构,使个人必须融入公共生活中,任何个体必须深刻理解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共同体内的公共生活在不断拓展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文化和共同记忆,并以此在社交层面和精神层面将个体纳入到共同体之中,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对“个体—共同体”关系的看法:尽管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存在边界,但并非截然对立,两者应该友好共存和互相促进。
个体与共同体都在不断变化与发展,因此两者关系亦不停更新变化。我们应同时兼顾“个体—共同体”的合力与张力,不能简单地认为将个体与共同体机械地结合起来就可行,而是要采取灵活和具体的方式,在微观层面保障个体自由与权利的同时,也在宏观层面维护共同体的稳定和利益,从而妥善处理“个体—共同体”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郑倩.浅析路遥《平凡的世界》[J].科技信息,2011(19):643-645.
[2]郝庆军.《平凡的世界》:历史与现实[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05):51-59.
[3]吴杰.《平凡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6(11):32-33.
[4]陈晓明.漫长的20世纪与重写乡村中国——试论《平凡的世界》中的个体精神[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07):1-31.
[5]王尧.冲突、妥协与选择——关于“八十年代文学”复杂性的思考[J].文艺研究,2010(02):19-23.
[6]张纯,宋川.美国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与冲突——谈谈涉及美国宪法的几个重要案件[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87(06):39-41+48.
[7]陈晏清,李淑梅.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观念的核心问题[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1):37-43.(作者: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廖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