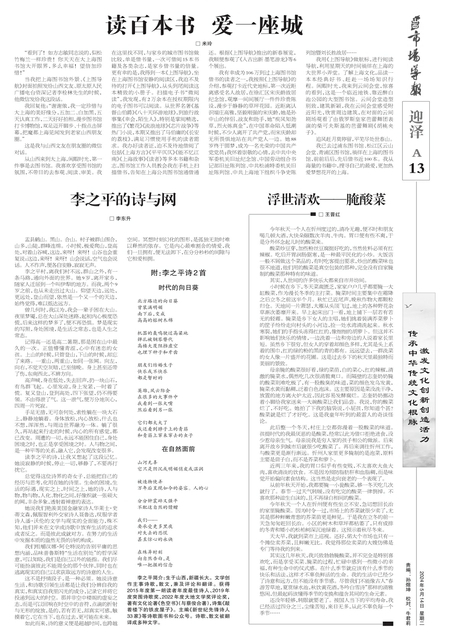李之平的诗与网
盂县鹤山。黑山。合山。村子被群山围合,山多,山陡,群峰连绵。小时候,极爱爬山,登高处,对着山谷喊,这边,来呀!来呀!山谷也会重复说:这边,来呀!来呀!山会说话,空气也会说话。人不作声,便各自安静,寂寂无声。
李之平村,离我们村不远,群山之外,有一条马路,通向外面的世界。她9岁,离开家乡,随家人迁居到一个叫伊犁的地方。而我,两个9岁之前,也从未走出过大山。仰望天边,远处,更远处,登山而望,依然是一个又一个的天边,始终觉得,难以抵达远方。
曾几何时,我以为,我会一辈子困在大山。夜里梦魇,总在大山深处迷路,起初内心极度恐慌,后来这样的梦多了,便不再恐惧。梦是现实的写照,身处困境,是生活之常态,也是人生之常态。
记得高一还是高二暑期,那是困在山中最久的一次。正值懵懂青涩,心中有迷恋的女孩。上山的时候,只管登山,下山的时候,却忘了来路。一重山,两重山,如同一张网。向左,向右,不觉天空灰暗,已至傍晚。身上甚至还带了伤,东南西北,不辨方向。
高声喊,身在低处,失去回声,扔一块山石,有鸟群飞起。心里发凉,身上发紧,一时着了慌。复又登山,登到高处,四下张望,仍不得要领。不由得泄了气。这一泄气,便万分地灰心,四周一片死寂。
手足无措,无可奈何处,索性躺在一块大石上,静静地躺着。身体放松,内心放松,什么也不想,浑浑然,与周边世界融为一体。躺了很久,再站起来行走的时候,内心的所有感觉,都已改变。周遭的一切,永远不能困住自己,身处困境之时,也正是享受困境之时。人与物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融入它,会发现改变很多。
读李之平的诗,让我又想起了这段记忆。她说寂静的时候,停止一切,够静了,不要再打扰它。
总觉得这位诗界的奇女子,总能把自己的经历与思考,化用在她的诗里。生命的困境,生活的际遇,现实之上,时间之上,她的诗,人与物,物与物,人化、物化之间,好像织就一张硕大的网,丰杂多象,透射着禅意的表达。
她说我们艳羡美国金融家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森,佩服智利外交家诗人聂鲁达,叹服学者诗人潘·沃伦的文学与现实的全面能力,殊不知,他们并未在文学或诗歌中放弃生活的追求或者反之。而是彼此成就对方。在努力的生活中发掘本质的盎然无畏的诗的构成。
我们咀嚼汉娜·阿仑特说的告别平庸的思想内涵,品味普鲁斯特“生活在别处”的哲学深意,可以知晓,我们是自己以外的能指。我们尽可能扮演彼此不能周全的那个伙伴,同时也在逃离现实的自己以求获取远方的诗意的人生。
这不是抒情段子,是一种必须。她说诗意生活,和诗歌引领生活都是让我们分辨自我的真实,和真实自我里闪光的成分,记录它并将它投递到远大的时空。那并非空中楼阁的虚妄之态,而是可以回响在时空中的音符,点滴的折射与无形的绽放,是的,若有若无,却真实可感,触摸着它,它在当下,也在过去,更可能在未来。
如此而来,诗的意义便是超越时间,也跨越空间。冥想时刻幻化的图形,是孤独无助时难以释然的依存。它是内心最难割舍的情爱,我们一旦拥有,便无法卸下,在分分秒秒的间隙与它相爱相拥。
附:李之平诗2首
时代的向日葵
北方路边的向日葵
曾装满明媚
南下后,变成
高高的榕树木棉
机器的轰鸣驶过高粱地
弹孔被钢琴替代
高楼大厦阻挡虚空
也埋下种子和牙齿
朋友们结婚生子
快乐或不快乐
都是暂时的
英雄,风云际会
在很多的大事件中
我看到一张大嘴
然后看到另一张
它们都太大了
我还看到脖子上的青筋
和青筋上窜来窜去的虫子
在自然面前
山河无辜
它只是阴沉或明媚俏皮或温润
被造物使弄
万年后呈现如今的姿容。人的心
分分钟震碎又强平
不配这自然的馈赠
我们——
要承受更多黑夜
对失去的恐慌
甚至惊心的永诀
在殊异时刻
向自然告白,是
唯一把握的信念
李之平简介:生于山西,新疆长大。文学创作主事诗歌,散文,兼及评论和翻译。获得2015年度第一朗读者年度最佳诗人、2019年度突围诗歌奖、2022年度大地文学奖评论奖,著有文化论著《色空书》(与蔡俊合著),诗集《敲着楼下的铁皮屋子》。主编《新世纪先锋诗人33家》等诗歌图书和公众号。诗歌、散文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李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