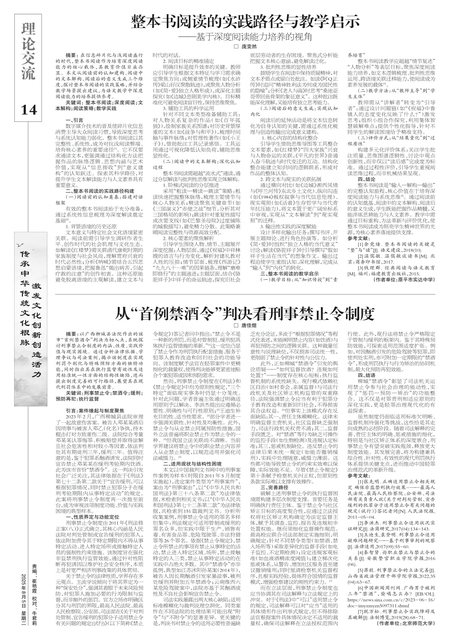从“首例禁酒令”判决看刑事禁止令制度
唐佳煜
摘要:以广西柳城县法院作出的该市“首例禁酒令”判决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刑事禁止令制度的内涵、性质、实践价值与现实困境。通过分析法律依据、学理争议与司法案例,揭示该制度在实现刑罚个别化与特殊预防方面的独特功能,同时指出其在执行监督有效性及适用标准统一性方面的结构性缺陷,进而提出制度完善的可行路径,展望其在现代刑罚体系中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刑事禁止令;禁酒令;缓刑;预防再犯:执行监督
引言:案件缘起与制度聚焦
2023年2月,广西柳城县法院审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被告人邓某某酒后因琐事与被害人邓乙(化名)争执,持木棍击打对方致重伤二级。法院综合考量邓某某认罪悔罪、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且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等因素,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值得注意的是,鉴于犯罪系酗酒诱发,法院同时宣告禁止邓某某在缓刑考验期内饮酒。此为该市首份“禁酒令”。这一判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其法律依据在于《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关于“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的规定。此案将刑事禁止令制度再一次推至前台,成为审视该项制度功能、价值与实践困境的典型样本。
一、性质界定与功能定位
刑事禁止令制度由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正式确立,其核心内涵是人民法院对判处管制或宣告缓刑的犯罪人,依法附加责令其于特定期限内不得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场所或接触特定人员的强制性约束措施。该制度旨在强化非监禁刑执行监管效能,通过针对性阻断再犯诱因以维护社会安全秩序,本质上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贯彻。
关于禁止令的法律性质,学界存在多元观点。主流学说倾向于将其界定为一种“保安处分”,强调其着眼于未来风险预防,对犯罪人施加必要的行为限制与监督,而非额外的惩罚。官方立场亦明确区分其与刑罚的界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禁止令规定》)答记者问中指出:“禁止令不是一种新的刑罚,而是对管制犯、缓刑犯具体执行监管措施的革新。”[1]这一定位凸显了禁止令作为刑罚执行配套措施、服务于犯罪人教育改造和回归社会的功能导向。该制度赋予法官在轻罪案件中更精细化的裁量权,使得判决能够更紧密地贴合个案犯罪成因和预防需求。
然而,刑事禁止令制度在《刑法》和《禁止令规定》中均为原则性规定,“三个特定”面临现实事务时仍显十分笼统。针对此问题,学者普遍主张通过明确适用原则予以解决。李洪杰提出应遵循必要性、明确性与可行性原则[2];王迪生补充目的性、适当性要求。[3]部分学者进一步强调关联性、针对性及均衡性。此外,禁止令与从业禁止同属预防性措施,国外立法普遍将职业禁止作为禁止令的一种。[4]但我国立法关联尚不清晰。当前学界建议将禁止令中的职业禁止内容并入从业禁止制度,以规范适用并强化司法威慑力。[5]
二、适用现状与结构性困境
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刑事案件案例为样本(时限自2011年5月制度实施起),选定案件类型为“刑事案件”,案由为“刑事案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为法律依据,未检索到相关文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为法律依据,共检索到151篇裁判文书。分析所收集案例,刑事禁止令适用的罪名多样但集中:刑法规定可适用管制或缓刑的罪名众多,但实践中限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危险驾驶罪、非法狩猎罪等26个罪名。依据《禁止令规定》,禁止令所禁止的事项有禁止从事特定的活动,禁止进入特定区域、场所,禁止接触特定的人三类,禁止从事特定活动的在实践中占绝大多数。其中“禁酒令”亦非孤例,典型如江苏沭阳孙某案(2014年),被告人因长期酗酒引发家暴滋事,被判处缓刑并附加五年禁酒令;云南维西六某危险驾驶案中,法院亦基于其酗酒成性及不良社会影响宣告禁止令。
司法实践暴露出两大核心缺陷:适用标准模糊化与裁判说理空洞化。同类案件在不同法院的处理结果可能出现“附令”与“不附令”的显著差异。更关键的是,判决书对禁止令的适用必要性普遍缺乏充分论证,多流于“根据犯罪情况”等程式化表述,未能阐明禁止内容(如饮酒)与再犯预防之间的逻辑关联。这种裁量任意性与说理缺位,不仅损害司法统一性,更削弱了禁止令的针对性与公信力。
此外,正如柳城“禁酒令”引发的舆论质疑——“如何监督饮酒?违规如何处置?”——制度存在核心短板:执行监督机制的系统性缺失。现行模式依赖社区自治(如村委会、亲属监督)与司法行政机关及社区矫正机构监管的双重路径,法院强调禁止令应当有利于犯罪分子教育改造和重新回归社会,不得损害其合法权益。[6] 但事实上该模式存在反面缺陷:其一,责任主体模糊化。法律未明确监督主责机关,社区监督缺乏强制力,司法行政机关权责不清;其二,监督手段匮乏。对“禁酒”等行为缺乏可操作的监控手段(如生物检测)及违规认定标准;其三,惩戒机制缺位。违反禁止令的法律后果未统一规定(如能否撤销缓刑),实践中处理随意,威慑力薄弱。这些都可能导致禁止令的约束实效难以保障,实际效能不足。尽管《禁止令规定》第十条赋予检察机关纠正权,但原则性条款实际难以支撑有效操作。
三、完善路径
破解上述刑事禁止令的执行监督困境需构建多层次制度支撑。首要任务是明确执行责任主体。鉴于禁止令与社区矫正目标的高度契合性,应通过立法授权将社区矫正机构确定为法定监督主体,赋予其调查、监控、报告及违规初步处置权能。继而须细化监督操作规范。最高检应联合司法部制定实施细则,明确规定:针对不同禁令类型(如禁酒、禁入场所等)采取差异化的监督手段(如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测);设定违规客观标准(如血液酒精浓度阈值);建立梯次化惩戒体系,从警告、增加社区服务直至建议撤销缓刑;同时厘清检察机关监督程序,扎根实践经验,提炼符合国情的监督模式,增强检察建议的刚性约束力。[7]
而在立法层面,刑事禁止令制度也应当协调其在司法解释与立法规定上的冲突。对于《刑法》中“可以”适用禁止令的规定,司法解释可以对“应当”适用的具体情形作出列举式规定,但不得排除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不适用的裁量权,确保司法解释在立法授权范围内行使。此外,现行法将禁止令严格限定于管制与缓刑的框架内。鉴于其特殊预防效能,可探索适用范围适度扩张。例如,对因酗酒引发的危险驾驶等犯罪,即使判处实刑,亦可附加一定期限的“禁酒令”,形成刑罚执行与行为矫治的协同机制,最大化预防再犯效能。
四、结语
柳城“禁酒令”彰显了司法机关运用禁止令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动性,实现了“惩罚—预防—矫治”的功能整合。这不仅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深化实践,更是轻罪治理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虽然制度仍面临适用标准欠明晰、监督机制待强化等挑战,这些恰是其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随着司法解释的完善、责任主体的明确、惩戒措施的细化,特别是与社区矫正体系的深度嵌合,刑事禁止令有望突破实践瓶颈,释放更大制度效能。其发展完善,将为构建兼具综合性、针对性、有效性的现代刑罚执行体系提供关键支点,进而推动中国轻罪治理范式的革新升级。
参考文献:
[1]张先明.正确适用禁止令相关规定确保非监禁刑执行效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答记者问[N].人民法院报, 2011-05-04.
[2]李洪杰.刑事禁止令适用状况实证研究[J].法商研究,2017(04):134-143.
[3]王迪生,袁登明.刑事禁止令适用疑难问题研究——基于刑事审判的观察[J].法律适用,2017(09):55-60.
[4]秦智贤.论职业禁止与禁止令的关系[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6(06).
[5]蒋毅.刑事禁止令的立法完善[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2,35 (04):63-67.
[6]中国新闻周刊网.广西男子被判三年“禁酒”,偷喝怎么办?[EB/OL].https://news.sina.com.cn/c/2023-06-16/doc-imyxmyzn5097311.shtml
[7]脱万松.刑事禁止令实践障碍及其破解[J].法制博览,2019(28):68-71.(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