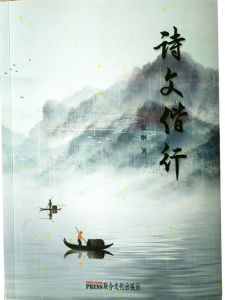与文化古都偕行
——张炯文集《诗文偕行》序
张炯先生祖籍河北,却是个“老大同”。他喜欢书画,跟我先期已经熟悉的书画家柴勇先生等是同学,并带我去收藏有不少清代及民国书画名家和大同早期书法家作品的他的姚姓同学的家去欣赏,我们自然多了一些话题。他喜欢古代家具的研究和收藏,还带我去拜访他的同学雕塑大师程晓钊先生。知道我自制木石印章,还叫我给他雕刻过木佛,并多次结伴去大同东街的古玩市场参观考察。他对民间文艺非常热衷,我们一起去位于西花园附近的大同莲花落研究专家李金先生的家去拜访,使我大体了解了大同曲艺的发展史。他热衷于撰写对联,每年春节报纸征联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并有入选,还多次一起去楹联协会;他常写一些散文、诗歌,时常见诸报刊;他非常热心,我在小品文选刊杂志社时,他发现好文章就常常带着一厚沓报纸荐稿……
《诗文偕行》这部文集,是张炯先生文字的荟萃,收集了他历年来主要撰写、发表的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近十八万字,虽然驳杂但并不轻芜,虽然量不算多但并不乏精品,这是他心迹的写照,是他精神的归藏,使我对他有了更丰富、全面和立体的认识,尤其读出了一位普通市民对发展大同古城文化的拳拳之心和对繁荣古都文艺的赤诚之情。
张炯先生的散文,主要以大同风情、怀旧、收藏为主。有的是写故居,如《旧居之忆》,虽然是写古老四合院的高大门楼、飞檐兽脊、彩绘砖雕,文脉隐伏,他却以此为背景,跳出了建筑文化、邻里相处的一般写法,而是颇对万字会这个曾经是“教会和有钱人在此行善事、赈灾民”“放粥”的地方情有独钟,挖掘石阶上斜孔、大方砖铺就的月台,及四角柱础的作用,从而不仅使作者自己种下了一颗普济世人的爱心种子,也使读者对大同的历史悠久和厚重文化容易产生景仰。他的散文《念妻》是写给已故妻子的,丝丝缕缕见浓情,一字一句有泪痕,因而令人感到情真意切,不由得伤怀良久。他的《扫楼道的女人》写的是一位“4050”下岗安置女工。“下到二楼时,看见她利索地清扫着楼梯角,尘土弥漫起来,一股呛鼻的土气,她看见我下得匆忙,马上立起身子来让道。眼前灰尘弥漫着,我略微犹豫了一下,同时,我注意到她的动作和眼睛里,流露出了那种歉意的神色”。这种细微的观察不仅刻画了人性之美,同时更产生了反躬自省的灵魂叩问:是我朝思暮想写的文章有分量?还是一个清扫女工无声的行动更感动人?得出的结论是她更胜一筹。他的《赏石三部曲》就说:“藏石所表现的形态,大概可以囊括世间万物,而藏石又有建筑、雕塑、绘画等静态艺术不能表现的空间,不夸张地说,静态艺术之美,藏石都可以表现出来甚至更多,在已经认定的形象上,我们的思维进行着各种联想和创作。于是,动物人物、山水花草、海天风云,都在藏石的境界中了。”我曾经送过他一块异形石头,他就专门写了一篇升华了意蕴的散文《石头花》。
张炯先生小说不多,大约只有四五篇,但都是对人性的挖掘,对生活的剖析,如《音障》《晨吼》《狗与门》等,颇令人回味,十分耐读,作家王祥夫先生当《云冈》主编时就比较荐赏。
他写了不少的诗,有现代诗,也有古体诗。他的古体诗也往往奇句迭出,富有极强的人生哲理:如《咏悬空寺》“来此幽僻无寒暑,去处宽阔有惊鸿”“凌空撒出伊人语,声声化入木鱼中”“悬寺谒罢心犹悬,常思足底临深崖”等等。
张炯先生尤其对古城大同具有强烈的挚爱。诗因时而吟,文为事而作。但更能代表他强烈情感的,我以为则是评论,是卓有见地、有的放矢、针砭时弊的建议性评论。这一系列真诚向好、赤诚向美、坦诚向善的评论,如《不可忽视的环境污染》《旅游节后话文明——一个亟待社会关注的话题》《对古城修复的几点建议》等等,更能彰显一位普通子民对具有厚重文化和悠久历史的沧桑大同为尽早实现繁荣、宜居和幸福而具有的责任、担当和情怀。愚以为,大同之所以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因为大同还有众多像张炯先生这样具有责任、担当和情怀的高尚民众。
张炯先生曾写过这样一首题画诗:
水墨凭渲染,韵气自潜神。
虽幼蹄疾奋,状态在不群。(原文为“不在群”,序者稍改之)
这首诗既是他对自我心性卓尔不群的流露和写照,也应该是大同大不同的核心内涵。
是为序。
作者系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大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