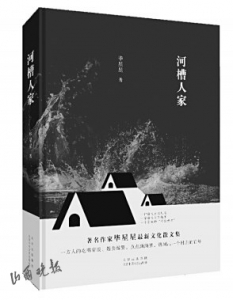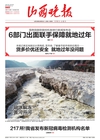关于中国北方乡村历史、文化、风物、景观的专书,《河槽人家》节选——
回高头村去认古碑
该书以散文记录一个村庄沧桑变迁的百年历史,描写了一方人的文化风俗,历史大势中亦有生活点滴。著名文学评论家阎晶明说该书是作者对自己乡土的一次认真的、郑重的致敬,是关于中国北方乡村历史、文化、风物、景观的专书。书中所写是作者故乡高头村的风光和人物,一个村庄的百年,沧桑变迁,移风易俗。作者意图通过真实书写,构建一个新的文学地理区域形象——“河槽”。
村长打电话来说,你回来一下,咱村里挖出一块石碑,都没人认得,你回来认一认。
我对古碑并不通窍,对我们村子的历史,当然知道一些。
我这个村子,是个古村落。村东南,有一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说明七八千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生活了。
村民多姓毕,这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史载为周文王第15子毕公高的后人。那么在春秋战国时代,此地应该就有村落人烟。
相传唐代李世民和窦建德隔河相对,这里是窦建德的大本营。李世民平定天下以后,将此地赐名高头李村。
最繁盛时期,此地曾经修筑武阳城,九门九关,清代嘉庆年间,涑水河发洪水,冲垮城垣,以后,就成了分散的几个村落,简称高头村。
村子靠着涑水河,这也是一条古老的河流。郦道元《水经注》有记载,司马光号称涑水先生,指的也是这条河。川地靠河,有史以来就是富庶地带。
也是由于富庶吧,人烟日渐稠密,人均地亩越来越少。乡亲们说,这里是人稠地窄。早在合作化时期,这一带就有民谣说:干的重活,吃的黑馍。说的就是河槽的日月。一年两季,小麦白面之外,不得不掺一部分玉米面吃。
乡村的日月,明显是分地以后好起来的。先是吃饱了肚子,再以后,这一带都栽种了果树,乡亲们都成了果农,收入高多了。
年轻的外出打工,靠的也是本地的历史传统,制作熟食,火烧烙饼麻花肉夹馍之类的,开个小饭店,一年也挣得不少。
靠着果树和小饭店,村子明显富裕了。我这一个庄上,八九十户人家,小汽车就有40多辆,当然不是投资生产型的,问买汽车干什么,年轻人都会说,不为啥,开着耍哩。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乡亲对故乡感情很深。不论到哪里开饭店,打出个小招牌,都叫“武阳饭店”,开个杂货店,叫“武阳杂货”。不论老人年轻人,都喜欢叙说村子的历史。“武阳城”,“高头李村”,是他们挂在嘴边的骄傲。
祖上的过去,虽然只是传说,口口相传,传了这么多代人,已经是奇迹。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的乡亲传下来,更是太难得的奇迹。
我匆匆赶回村里。大半年没有回去,村容村貌又有变化。一条宽街道打成水泥了,不必说。全村所有的街巷,哪怕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巷,也全部硬化成了水泥路。
几条主要干道,架起了新款太阳能路灯,电线杆头顶扛一个白亮的平板,路灯成了景观。演戏的舞台也新修了。台下的戏园子一展儿铺了水泥,成了一个文化广场。
村长迎了我,把我带到台口右侧,新发现的石碑已经坐好了在那里。立在台口一侧,位置很是显眼。
碑首半圆形的,两条青龙攀绕,有云纹衬着。碑身刻满了文字。碑座一半嵌在地下,一半在地上,露出平整的台面。
这一座石碑,村长说,是从全村南北三个不同的地点挖出来的。碑首堵在一口机井的井池里,碑身让前巷拉了去,垫在浇地过水的壕沟上。碑座没人搬得动,湮埋在地下多年了。为了搜寻这三大件,村长动了汽车,吊车,铲车。
村里年纪大一些的都认得,这一通古碑,原来安放在我们村里的关帝庙大殿。
高头村的关帝庙,规制较大,占地有10几亩,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大约在1960年代大庙就塌毁了,石碑埋压在废墟里。
到1980年代,大殿对面的戏台也拆了,关帝庙随即成了一个方位,一个符号记忆。又过去20多年,大庙原先的遗物呢,一件一件就下落不明,杳不可考了。
你得服气,这个村里就是有一些有心人。县城中学的一位老教师退休在家,他像一个侦探,住家多年以来,一直在打探几通石碑的下落。知道了,也不能张扬,生怕文物贩子倒卖了去。
前几年,他终于认定这个村长可靠,临去世之前,把这座身首异处的古碑的三个具体地点详细嘱托给了这一任村长。托付了遗愿,老人放心地离去。这才有村长兴师动众打捞安装的壮举。
我靠近石碑,仔细看那碑文。
古碑上方中央,有凹下去的一个方块,嵌刻“敕赐洪教禅院”,行书。
上首自右而左,有大字“尚书礼部牒”,行草。“中散大夫行员外郎李”“宣威将军郎中耶律”等字样,行书。
碑文记载起事由为:
河中府猗氏县高头李村僧智通并百姓李义真等多人均等伏纳钱一百贯,承买到本村僧院一所,计舍一十九间,敕牒乞书填作洪教禅院者——
时间落款为:
时大定十四年十二月戊午朔望後三日
这样,我就大体明白了这座古碑所记载的事情。
金代大定十四年(公元1165年),高头李村一个和尚智通牵头,联络村民买下一座院子,19间房,设立一处禅院。
报请朝廷,赐名为洪教禅院,由礼部发文通知,一个姓李的员外郎和复姓耶律的郎中操办此事。二位,应该是今天的部长级干部啦。
我有一种云散天开,日光融融的感觉。这一通碑文,证实了起码在金代,这里就是一个像样的村落。也间接证实了,所谓李世民御赐“高头李村”不是虚妄之言。
一通石碑,接通了八百多年前的根脉。思接千载梦悠悠,我终于和800多年以前的老先人对上了话。这个村子终于又找到了先人留下的千年谱牒。
村长早憋不住了,急切地问:这碑,有意思吗?
我说,现在还不好说它对国家有多大意义。但是对咱的村子,那可是意义大得很。
现在都说村委会主任,农民还是习惯叫村长。村长不过40多岁,其实也就上了个中学。要说历史知识,实在不知道多少。为什么对一座古碑这样情切意长?
还有那个中学的老教师,持续多年寻找一幢遗失的石头。还有动员起来的村民,搬迁安放,在他们心里,这就是一样神器。
要说文物价值,这块石碑不算怎么金贵。他们不能释怀的是,这块碑和自己的先人活动有关,和这个村庄的过去有关。
追祖敬宗,思古怀远,这样一种朴素的情感,驱使他们在田野上爬梳钩沉,终于找出了祖宗的千年遗留,供在了全村的最显眼的地方。
为了庆祝文化广场落成,村里这番请了剧团。自从竖起这一幢古碑,每天都有人观看摩挲。青石头,很快印满了村人的手印。我不能阻止他们,谁好意思阻拦离散多年的亲人泪眼执手相看抚摸呢。
一些上了年纪的,更是终日围绕不散,时不时给后生娃娃讲一讲当年关帝庙大殿的场景。那是石碑原来的坐落,也是他们看到的古碑的历史。
几十年的光阴,失而复得,他们的讲述,后人复又传给后人。口口相传,乡村的文化接替,就是这样完成的吧。
文化官员下令保护文物不奇怪,文物专家奔走呼吁保护文物不奇怪,你见过一群大字不识的农民这样珍爱村庄的历史物件吗?
我们的大地,曾经是一个古迹罗列,文化神器星罗棋布的大田野。
我小的时候,村子里关帝庙、娘娘庙、药王庙不下头二十个,庄稼地里也时时可以看到点将台、文笔塔一类古建。那时行走在乡村,就是在文化古物的丛林里穿梭,你随处可以和千年的历史对话。
经历了1958年的破除迷信,“文革”中的破四旧,千年古物所剩无几。
这几年又有专家说,文物古迹的摧毁性破坏,在于经济腾飞、城乡建设大规划这几年。一片一片建筑新区,覆盖了城市,铺遍了乡村。
高头村呢?生活富裕了,小楼盖起了,小汽车买下了,我的乡亲们却在千方百计细心地保护自己的历史。
新农村建设的浪潮铺天盖地,几百年未有的大型横扫正在千万里江山如雷滚过,这里一群布衣布鞋、粗茶淡饭的乡民在倾心保护自己的祖辈遗物,让人感动。
村长委托我,回到省城找几个记者,把咱村的老石碑上上报纸!看着他殷切的眼神,我答应了。
在山西,我曾去过张艺谋拍电影的老井村,那个村子大部迁出,已经接近废弃。这几年,也多次到过北路一些村子,一个村子留下三五户,进了村子点数,不过八九个人,两三条狗,十几只羊。乡村的凄凉惨淡,令人心忧。
我骄傲,我的村庄不是这样。村庄新路新楼,遍野果树,环境优美。留守的务果树,即便在外打工了,也很少在外落户,存了钱还是要回村来盖房子娶媳妇。
村庄为甚有这么强的向心力?历史文化的凝聚力不可小视。先人的足迹踏过几千年,脚下的土地是一块踏实了焐热了的土地。
村落的过去,有着千年书写,每一副面孔后面,都有无尽的沧桑动人的故事。这个村庄蕴含着多少朝代,多少江山,多少人事,你就越发舍不得离开他。
村落如果没有自己的历史,那不过是一滩住了人的房子,又有什么意思。
你想明白了吧,我的乡亲,哪样欢天喜地,哪样神圣膜拜,供起了这样一座古碑。
我的村子,真是一个好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