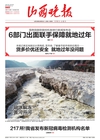用匠心呵护三晋大地的艺术遗产
本书为作者近十年来对艺术遗产的思考、田野与反思汇集之作,涉及古村落保护、陶瓷窑口文化遗产、晋商建筑文化遗产、宋元明清绘画遗产等,大者可看到榆次的后沟古村,小者可深入于晋商大院之中;向古者,追溯到“千年窑火”,如对介休陶瓷艺术遗产进行了解读,往后者则聚焦于“美美与共”,以当代的视角对艺术遗产进行了诠释;既有学理之思考,又有“吾情吾作”的真性情流露;既有以文字精雕细琢之“遗产”,又有以画笔饱蘸五彩之“画作”,融思想性与学理性于一体。
一本好书,总是能唤醒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细细翻阅晋中学院刘小旦副教授的著作《走向田野与艺术——关于艺术遗产的对话与反思》,厚厚近400余页,但读起来却并不吃力,图文并茂、语言优美,每章的切入口都很新颖。书中既有对山西榆次后沟古村、介休窑瓷器、晋商大院的客体解读,也有对古村落保护、艺术遗产当代诠释的问题研讨,字里行间,蕴含着对艺术遗产传承与创新的深层次思考。
艺术遗产的最大魅力在于遗产自身,如同榆次后沟古村和介休窑,有其独自的“生命旅程”,它们的经历也许谈不上惊涛骇浪,却时而水光晴和,时而阴雨密布,甚至电闪雷鸣……古村落是一坛老酒,时光暴晒,生活发酵,美学提纯;而介休窑则是一场千年不曾熄灭的窑火,烧造了我们日常的器用。也许乍看作者关注的只有冗长的日常与琐碎,可正是在这样琐碎的日常中,一些不起眼的细节与多年前另一个细节的偶然相遇,形成一个个带有深深文化印记的艺术遗存:小到床头的布老虎与炕围画、剪纸与绣花鞋垫,大到村落的风水与营建理念,再到社会意识与多神信仰。艺术遗产在古村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因为艺术源于生活本身。
没有生死传奇与激荡跌宕,却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作者用安静的文字,行者的语言,画者的笔触,将十余年的田野调查原原本本呈现给读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回归艺术遗产考古现场,让艺术遗产自己说话,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纵览全书四个部分,因为描绘真实而倍感亲切,因为说理透彻而富有启示,针对典型山西艺术文化遗存,下功夫、重细节、小切口,不仅完成了对艺术遗存的解读与记录,也将读者引向疼痛与思考。
如作者在书中追问到在工业高速发展的时代,以后沟古村为代表的山西传统村落大多面临着城市化、商业化、物质化的发展困境与文化冲击,如何进行保护性开发?如何实现“老树生新芽”?如何推动创造性发展?这是山西古村落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
他给出的答案是“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新旧共生,和而不同。作者在扎根田野的深入调研中认识到艺术与社会、美与生活相互交融的特性,他运用村民文化自觉的理论,解析了村民在古村保护中发挥的作用与承担的责任。他在书中指出:“古村落的保护根本上讲就是古村落的主体村民对古村落自身文化传统的自主自觉”,“文化再生最终只能由古村落的文化主体村民来完成”,这为当下解决古村落保护困境提供一条有益的探索路径。正如该书所言:“我们不是单纯对古村建筑的保护,也不是单纯的旅游开发,而是要发挥村民主体作用,保护‘一个农耕文化的整体’,即‘北方黄土高原农耕文化古村落的文化整体’”。
受绘画专业思考习惯的影响,在艺术遗产的田野调查中,作者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褪去厚重的历史外衣,用一种更偏向艺术的视角去理解历史文化遗存。因为艺术不分国界,不分语言,不分时间。艺术可以抛开一切外部的环境而根植于人的心灵,无论何时何地,何年何月,心灵对艺术的感受总是相通的,正所谓“非贵乎其文辞,而贵乎其心底也”。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十余年来,作为一名地方学者,作者始终执着于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执着于艺术遗产的探寻与传承。走向田野,走向艺术遗产,即是走向文化的根,走向民族的魂,力透纸背的是作者对艺术遗产独特的思索与体悟。
美美与共,久久为功,发现与守护艺术遗产,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与传承人的参与、呵护与激励。时代呼唤着更多的艺术家与建设者,用匠心呵护遗产,以文化滋养社会,用艺术守望未来。
刘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