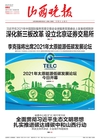新雁两三行
“嘎,嘎——”每临秋日,午夜梦回,耳畔常传来数声雁鸣。即便闭上眼睛,我也能从声音中分辨出哪是老雁,谁为新雁。
于雁,我喜之久矣。孩提时代,我生长于江村,一俟秋日,经常看见大雁——车行有轨,雁飞有道,那弯江流,即是“雁道”。雁飞行时,极具飘逸之美。夏日去后,凉意袭来,江草凝碧,风生水上,烟色青苍,飘来荡去,人一旦凝望久了,心会被慢慢濡湿。
雁特守时,纪律尤严。江岸有一高坡,乡人称之“观雁台”,此台,据村里老人讲,它历越千载,故垒西边,曾是古战场。从稻田收工,人牛俱疲,为此,父亲常令我牵牛至台下,一则饮水,二则放牧。恰在此时,从夕阳沉沦一方,“嘎——”,一声嘹亮的雁叫声传来,声彻天地,分外悠扬,这一声唳叫,饱含世间沧桑,挟带千载古意,让人禁不住翘首以望,喜极而泣。
斜照熔金,红中带灰,灰里泛紫,沉沦之中,落霞不飞,唯见一队队雁破空而来,迤逦不绝,如神兵行空,天将摆阵——雁飞于天,那身姿,仿佛是一个个飘逸优美的汉隶,挥毫西天,洒脱至极。仔细谛听,雁儿扇动翅膀引得空气咝咝作响,仿佛一股股电流从耳膜传至心尖。
为了近距离观雁,我将老牛牵上观雁台,站立牛背,一动不动,状若青铜。余晖脉脉水悠悠,雁群就在眼前,“哟嗬——”,我将双掌拢成喇叭,喊了一声,一只头雁听见我“打招呼”,侧过脑袋,看了我一眼,褐色的眼眸里写满温存——也许在它的眼里,我也是个不经世事的蓬头稚子呀!
“嘎——”,它回应了一声,继续飞游。其实,我最爱的是新雁两三行。也许是首次南飞,它们既怯,又好奇,自行组合成阵,扑扇着浅栗色的翅膀,也学老雁嘎嘎而鸣,如胡琴新试,极富活力。它们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摆成“人”字,调皮又可爱。
雁落时分,又是另一种美!
天色欲晚,行程漫漫,只好夜宿。当落日缓缓沉江,烟敛霞收,周遭最后只剩一线温煦的余光,当雁群冉冉而下时,江村苇塘顿时热闹了起来,不!准确地说,应是嬉闹。嬉闹的原因,不仅在雁,而且在鸭。这些鸭,是野鸭,常年生活在池塘。当雁群遇上鸭群,“物以类聚”,仿佛他乡遇故知,鸭们如主人一般欢迎雁群的到来,大雁如宾客一样受到热情的接待。
一开始,小雁们还不适应,但有老雁呵护,胆子渐渐大了起来,很快与小鸭们打成一片,形如兄弟姐妹,亲亲热热,击翅而鸣,拍水而啄,难分彼此。一片塘,仿佛一鼎沸水,惹得村童趴在野蒿白茅间偷窥。待到月上柳梢头,热闹了好一阵子的池塘渐渐安寂了下来,到了夜半,白露垂江,萤飞草塘,偶来小风,窸窣作响,同时,也送来了小雁梦呓,稚稚嫩嫩,一两声。
在我的印象里,在江与村之间,有一方名叫“回塘”的大水,长有黄芦苦竹,红蓼紫苋,冬暖夏凉,俨如小江南,每一年秋暮,总会有几只新雁留下,与鸭为伍。
一晃,到了来年,从南空又传来嘎嘎之鸣,新雁闻之,拍翅而起,加入雁阵,千山万水,迢递云间,回归塞北。一代代雁群,一年年雁回,一秋秋新鸣,都是为了奔“故乡”。
如今离别故园太久、太久,在这个秋晚,我能循着记忆里的“故道”,与新雁为伍,一路飞歌,回到乡关吗?!
□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