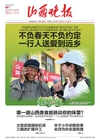细说从前——一个80后的这20年
孰对孰错
我小时候,看病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在山村的卫生所里,只有“吗啉胍”“抗菌优”等寥寥几种药。生了病就得去城里的医院,不愿意舟车劳顿就只能挺着。
有一年暑假回村,我闹起了中耳炎,疼得整宿睡不着觉。妈妈无奈之下只能把牛黄解毒片碾碎,用水调了给我灌到耳朵里止痛。结果病没好,干脆失聪了。没奈何,还得赶紧去正规医院看病。拖拉机转公交、公交转火车,好容易到了省城。大夫一看:“这是谁干的,胡闹!”妈妈红着脸站在一旁,悄悄看着大夫为我掏耳朵。我咬牙忍受着,每一秒都好像在遭受着酷刑。好在大夫医术精湛,一小会儿就清理干净了。然后拿出个小瓶,用棉签蘸了点不知什么药水一擦——毫不夸张地说,耳朵立刻就一点都不疼了。大夫批评妈妈说:“小毛病也得及时治,可不能自己乱来啊。”妈妈则嗫嚅道:“没办法,村里实在没有医院……”
好在,我的儿子不用再为一点小毛病担心了。我所在的城市虽然不大,但医院也有好几家,自己还有车,无论什么时候需要,上医院用不了几分钟。所以这些年来,尽管他闹过几次毛病,也都是有惊无险,很快就云开日出了。
但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那年初夏,幼儿园里流行起了“手足口”。虽然我们刚得着消息就暂停了托管,但这小子还是中招了。起初是发烧,无论吃什么药都不退。继而手掌脚心都开始出疹子,红色的小点密密麻麻,看着就揪心。大周末的也顾不上了,赶紧送医院呗!附近的那家“三乙”,放到全市也是有名的,儿科实力雄厚,大夫经验丰富,那几年我可没少往里跑。
来到医院,正巧遇到一支奇怪的队伍。有几位穿了白衣白帽,更有十来位做了各式打扮,拎着棍棒、打着白底黑字的横幅,气势汹汹地簇拥在周围。我无心细看,赶紧抱着孩子绕了过去。匆匆跑到挂号室,本来想挂急诊,护士小妹提醒我:“不如去儿科病房找主任吧,比急诊大夫更专业一些。”于是我便马上出门奔向住院部大楼。
也不知大夫在哪里,正准备找人打听,就听有人问道:“您有事吗?”回头一看,是位看起来很面善的女士,仔细一想,不正是我求诊过的一位大夫吗?“太巧了!”我欢喜地轻呼起来:“大夫啊,我儿子烧得厉害,门诊又不开,麻烦您先给看一看吧!”女士闻言略一犹豫,但还是俯下身来,和颜悦色地让孩子张嘴。只一打量,就确定地说:“是手足口病,你看,已经出现草莓舌了。”“那您看这是打针还是输液啊?”可谁承想,大夫却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几番欲言又止,最后还是道:“咱们现在不收治病人,要是实在退不了烧,我可以让护士帮孩子灌灌肠。你赶紧想办法往市传染病医院送吧。”
眼见着孩子越来越蔫,我心急如焚又不好发作。医者仁心,不收病人是啥道理?软磨硬泡之下,大夫思忖再三,才下了好大决心似的带我下了楼,转进了发热门诊的临时病房里。到了地方,她就没空再理会我,只顾忙着给孩子灌肠、输液。等都安顿好,才带着一脸的憔悴走了。我感激之余不免疑惑,便和护士大姐打听。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儿科刚出了医疗事故,家属正天天跑来闹事呢。那位小患者原本只是发烧,家里没怎么在意,只随便喂了点药拖着。直到越拖越重才送来,一检查已经是脑膜炎了,虽然历经抢救,到底没救回来。
如此悲剧的确令人唏嘘,但大夫再神也没法起死回生啊?护士大姐叹了口气,接着说:“没办法啊!完全成了一场讹诈。这两年有不少儿科的大夫都转了科室,长此以往的话……唉!”
孩子的烧已经渐渐退去,耳边传来了他粗重却已平稳的呼吸,可我却越发焦虑。窗外的悲号声让人茫然,孰对孰错我也无权置喙。但医疗条件明明越来越好了,可给孩子看病这回事,真怕以后更难。
在水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