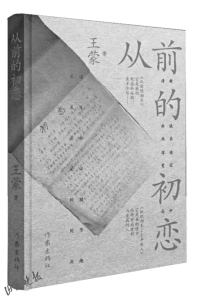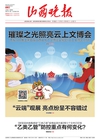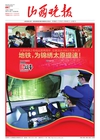历经六十多年首次面世,王蒙日记体爱情小说《从前的初恋》节选——
缘起
《从前的初恋》王蒙 著
作家出版社
该书由中篇小说《从前的初恋》《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及老照片组成。1955年前后,在创作修改《青春万岁》的同时,王蒙插空写下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与《初恋》。这篇日记体爱情小说当时未能发表,手稿在大半个世纪后的2021年被作者发现。八十六岁的王蒙面对二十出头时写下的十八岁恋情,心潮激荡,提笔在原稿中穿插写下心曲,是与从前的对话,也是导读,旧篇添新章,构成了《从前的初恋》。
从前,有这么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儿,一个是女孩子。
他们是唱着“我们的青春像火焰般地鲜红,燃烧在布满荆棘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地英勇,飞翔在暴风雨中的天空”长大的。
他们也都曾唱着“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那光明的路”向着高压水枪与刺刀冲锋。
从前,就是说七十多年以前了,一次,曾经,仍然,最初的,爱。
后来,他,也就是我,找到了曾经写下的这一段故事,稿纸已经变黄、变脆,文字依旧完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具店的蘸水钢笔、稿纸、骆驼牌与北京牌墨水,还有少年王蒙的写作,经受了相当长期的考验。倏忽一别,六十六年。
但想不起写作的确切时间。应是一九五六年稿吧,根据是一九五六年一月全国主要出版物由竖排改为横排,而作者书写使用的是那一年市场开始提供的大张单面横写500字型格纸,此前的稿纸都是折叠双面竖写小张的。这一年公布了首批简化汉字,文稿上写的却是大量不规范的民间简体字。
如果确是一九五六年,那么有趣之处在于,它与同年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互通互生互补互证同胎同孕异趣。
给过一家刊物,回答是“不拟用”,退还。然后六十六个春秋来去,从北京西四北三条(报子胡同)、北新桥到乌鲁木齐南门、团结路,到伊宁市解放路、新华西路,到北京前三门、北小街、奥森公园……经过了“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引自旧作)的迁移,许多东西都丢失了与淘汰了,此旧稿却完整地、寂然冷然地保存着,坚守着,与我为伴,我再没有翻起过它。它与我共度了两万多个不平凡的日夜,比我本人更静谧、耐磨、沉得住气。
它是我的纪念和从前,直至今日。
至于文稿内容,写的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七十年后心血来潮,打开,热气与稚气腾腾。它是往事,是昨天,比昨天远,但比前天近。仍然保留着笑容、多情、歌曲、好梦,包括“最宝贵的”(一九七九年我的复出小说的题名),包括一条条大义凛然,永生永世,天地人心,必须、笃定、坚决、当然。
我尽量少动原文,原汁原味。日记体,是因为一九五六年前五六年,我确实坚持写过详尽的日记。此后小说写多了,公务事务也大增了,日记基本失守失踪失忆,写也不成样子了。小说与公务事务,对于日记,是推动也是妨碍。不太忙也不太不忙的人可以试着写点小说,不然就写点日记手记,留点印迹。
到了一九五六年,写作此稿时,参考了抄录了移用了几年来的“非虚构”日记,包括某些日子的天气标记,应该都是有根据的。从前的真实日记,写在三十二开横线笔记本上。在《组织部……》轩然大波之时,我写下了孪生的《初恋》。
往事如烟?非烟?那么请问:你是谁?你是不是文学地写了下来?你生活得很急很热,你写得很动情很火,晾了一点一个甲子,它仍然乒乒乓乓欢蹦乱跳。文章何处哭秋风(李贺)?如火如荼势如虹,且掬黄河泼大墨,文心文气岂雕虫!
1951年12月23日 星期日再有一个星期,光荣的、伟大的、深沉的一九五一年就要过去了,时间如飞,小心自己不要落在时间的后面啊。
到了冬天,到了新年,我就想起雪,白白的、可爱的雪,雪使世界庄严而纯洁。今年寒冷偏偏来得晚,一场正经的雪还没下呢。
一九五二年我就年满十八岁了,的确,年龄自有它的真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感觉到,我已经大了,我已经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有多少力量、又有多少幻想啊。
从前我为自己年龄太小而羞耻,好像一株小树,没有发育好,就生长到伸展到风暴里去了,结果年龄,嗯哪,妨碍了我的工作,这样一说,我觉得自己不免失笑于众。众精灵、老干部,革命与战争培育出来的精明与犀利的一代,他们怀疑地打量我并且信且疑地询问我的岁数,当别人窃窃私语“团区委来了一个小娃娃”的时候,当我不能参加某些正式党员的会议的时候——我入党三年多了,岁数不够,还没有从候补党员转正,我总羞愧于自己为什么小,如果大一点,就更可以有所作为了。
现在呢,不再想这些,没有人怀疑我不是二十多岁。区委书记老伴,办公室的老田大姐,从一开始一直称呼我为“老刘同志”,工作里,我已经显示了一点点沉着与老练。本来嘛,成为脱产干部已经三年了。
环顾四周,朋友、亲人们,也已经有了许多变化。爸爸和妈妈离婚了,这很好,也很不容易,结束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十年的残酷和痛苦的变态,固然还有尾巴。最近几个月,我首次在家里感觉到了平静和幸福。姐姐从学校出来,走上了工作岗位,她变得沉稳而且严肃。上次她批评我不该对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兴奋与入迷:滑冰、小说、唱歌、欣赏风景……说话也不应该动不动夸张激动。她提出要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工作和学习中,对极了。她还告诉我,她已经有了一个男性好朋友了。
过去我觉得,她虽然比我大一岁半,可是我帮助她在政治上“进步”起来的,而最近,我越来越感觉到,许多地方,是我需要向她学习了。
还有学校里的一些同志,中学的团总支干部们,我与他们的亲密,超过了与本机关的同事们。说实话,他们身上的担子够重的。一个中学生,每天七节课,团区委给他们布置了繁重的任务。就说两次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吧,他们下了课后与校长们一起做新生审查工作,同学们对他们的要求又特别高,一次早操缺席,同学们就会说他们是“带头作用不够”。结果呢,一个学期结束了,他们的考试成绩比一般同学还要强,甚至于,他们学会的新歌与集体舞、新诗与新知识,即使是读报,也比其他同学们读得更多。
我常常回忆今年年初参与的中学生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的情形,这些孩子们自我检查起来,比谁都沉痛,眼泪会在检讨会上流下。不,这是保尔·柯察金式的对自己的苛刻与无情。他们如果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些不利于党的缺陷,会万分地痛苦。高兴的是,培训班结束后,他们一一地入党了。小李还送我一本“革命日记”,其实是我应该送他们一点什么纪念品的。我也怀念参军上了干部学校的同志们,前天,收到建群的信,他们马上要开赴朝鲜前线了。而省立高中的地下党第一支部书记,参军以后立即保送到沈阳的空军学校,他将驾驶着战鹰在蓝天白云中万里飞翔,与敌人短兵相接,瞬时胜负存亡生死。我羡慕他们,也祝福他们。
我们这里的张昌,常常嬉皮笑脸地叫他们“小干部”,我不喜欢。老有老的伟大,小有小的庄严,不容亵渎,不容轻薄。
我自己呢,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们的书记黎银波近来几次颇有深意地对我说:“你很不错,你真的大了……”可以想象,比我大十七岁,抗日战争前“一二·九”时期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她,对于火爆的小人儿刘夏有多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