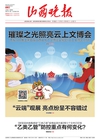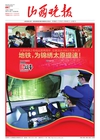带我走上写作之路的一本书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从六七岁开始阅读到现在近四十年时间了,读过数不清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可是这么多年来也仅仅停留在阅读的层面上。写作,于我而言似乎是极其遥远的事,我似乎也只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阅读者。可我没有想到,散文集《阳光下的蜀葵》在我生命中一出现,竟汹涌地触动了我灵魂深处深埋的乡村记忆,打开了我内心渴望写作的文学情结。
2017年元旦刚过,武乡大地朔风凛冽,小雪霏霏,在民间颇有影响力的文化桥梁“家乡之音”年会热热闹闹地召开了。年会上,我不仅认识了作家蒋殊,还得到了她亲笔签名的《阳光下的蜀葵》。拿到书的当晚,我就迫不及待地在灯下开始阅读。
这是蒋殊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她写给自己村庄与家乡的一本书。蒋殊这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作家,当她敲击键盘要写第一本书的时候,童年和少年17年故土生活留下的烙印,自然而然地拨动了她的心弦,让她用不着选择就走进了怀乡这个主题。那个寒冬的夜晚,蒋殊的娓娓叙述如同蜀葵发散的屡屡清香,氤氲了我的小屋,丝丝缕缕地渗透进我的心灵深处。
散文大家张锐锋老师在书序中这样说:“蒋殊用她特有的朴素的笔触,把她所熟悉的、热爱的人们,以及这些人们生活的境况,画了出来,并涂上了色彩。面对眼前的人们,她不是遥望,也不是简单地观察,而是近距离地感受和对视,这使她的文字被赋予了体温和心跳,以及充满了爱和哀伤的眼神。”确实,刚读文章时,我就被蒋殊朴素的文笔打动了,那些花儿、那些果实、那些人们在她的笔下都灵动起来,故乡的秋夜是那么的静谧又那么充满温暖的味道。读着,读着,我不仅仅读出了文学的味道,更读出故乡的味道。文章里出现的哪里仅仅是她的村庄,她的亲人,她故乡的风土人情,分明也是我的村庄,我的亲人,我故乡的风土人情啊。我们的村庄都是一样的沟下岭上,都要在下雨天饱受泥泞之苦,干旱时节一样要起早去井边“刮水”;给予我们温暖的至爱亲人,一样饱尝了生活的无奈和艰辛;淳朴善良的乡亲,秋天一样要累得伤痕累累,一样有小农的“劣根性”;我和她少女时代,一样在心间珍存着少女的粉红心事,一样有回忆起来忍俊不禁的糗事;甚至那充满着故事的老井,还有那烂漫了一院生命力异常顽强的蜀葵花……我们俩故乡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相似,都是那样的贫穷、安静,却又充满生活的温暖气息。
可是,蒋殊的乡村还在,而我的泉江村却已经移民到了监漳村,地理意义上的泉江村正在慢慢地消失。2016年11月,我陪母亲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泉江村。村子里已经荒无人烟,只有通向农田的小径告诉我们这里还有村民活动的足迹。老屋,满院的衰草没过人膝;房屋倾圮坍塌、残壁断垣,几只麻雀从倒塌的屋角处惊飞出来;门窗洞开,屋内满地狼藉,小动物的粪便、杂乱的木块、墙上掉下来的泥皮随处可见,弃用的瓮瑟缩在墙角;曾经的灶台不见一点儿火星,被煤烟熏过的墙壁上挂着一串串蛛网。门前大槐树下曾经热闹的饭场,一地枯黄的落叶;对面土丘上的人家,黄土窑洞已经完全倾覆,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窟窿,让人依稀可辨。
曾经,村里有两棵富有标志性的树,一棵杨树生在奶奶庙附近,淡青色的枝干笔直向上,裸露的根部暴露出地表,遒劲如老农手背上暴露的青筋,延伸到周围一两米远后又重新扎入地下,村民把这些树根当做凳子一样坐在上面休息。树上挂着村里唯一的高音喇叭,三中全会、联产承包等政策全部都从这里收听。另一棵是老榆树,长在全村的制高点——龙嘴上,粗壮的枝干斜伸到悬崖边来。每到春季,开满了豆绿色榆钱的枝条随风飘拂,仿佛向我们报告春天的信息;树干上挂一截铁轨,只要村里有大小事情需要开会,队长就会敲响铁轨,大家就陆陆续续走到集中地吵吵嚷嚷地商议。这两棵树都见证过村庄的改革变化,了解乡亲们的喜怒哀乐。如今抬头搜寻,它们在哪里?杨树生长的地方光秃秃的,不见任何踪影;而老榆树,只留下一截被雷劈后的黝黑树桩,孤独而悲伤地守望着。
行走在坑坑洼洼的黄土道路上,内心忧伤而又甜蜜。我曾在这些路上兴奋地跟着父母去地里干农活,体验劳动的欢乐和艰辛,可如今父亲却已离开我们十多年;我也曾和隔壁哑巴三奶奶比比划划着一起去捥猪菜,建立起了忘年交,可三奶再也看不到我的比划了;我曾和同伴们一起打闹着上学嬉戏,黄土道路开启了我们人生理想的篇章,可如今理想还在彼岸,同伴们却早已各奔东西……
捧着《阳光下的蜀葵》,思绪却要这样一幕幕热烈地翻滚、蔓延,压也压不住。我吃过东家的蒸饺,喝过西家的和子饭;摘过李爷爷家的杏,尝过王大娘家的桃;听过大人之间的争吵,也见过他们困难时的互帮互助;寒冬腊月在坡上滑雪,炎炎夏日在僻静的河里洗澡……《阳光下的蜀葵》就这样轻易拨弄出我脑海中深藏的故乡山水、草木、人物。突然就泪眼朦胧了,这才是我的故乡啊,是有别于蒋殊的故乡、有别于其它任何地方的我的故乡啊。
而被我深藏了多少年的故乡,是不是早就应该把对它的魂牵梦萦诉诸纸上?我这个村庄的孩子,是不是也应该为故乡书写些什么?我是不是,也应该用我的笔,让人们知道泉江村,记住这里曾经的一些人,一些牛羊,一些树木?甚至一条泥泞的小路?
2017年的1月7日的晚上,于我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阳光下的蜀葵》一页页墨香穿透纸背进入我的灵魂。窗外寒风凛冽,我却周身温暖。我在激情的驱使下当即拿起笔,尝试写下第一篇不成文字的文字。我意识到,不能让我历尽沧桑的故乡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应该让内心积蓄的文字慢慢跳出来,为故乡,为土地,为有声与无声的事物,留下一份记忆。
从此,我不仅仅只是阅读,而是拿起了笔,写下一行又一行,一篇又一篇文字。遇到瓶颈时,我就一篇篇翻看《阳光下的蜀葵》,学习每一篇文章的选材,研究每一篇文章写作的角度,甚至其中的遣词用字我都细细斟酌。我知道,与古今中外读者耳熟能详的名著相比,还有许多人不知道《阳光下的蜀葵》,但万书丛中,它恰恰就是那一抹红,触发了我写作的情思,带我走上写作道路,更成了我学习写作的教材。
一年多时间,我为故乡写下十多篇文字,记录下许多被人遗忘的风土人情,拉回了许多渐行渐远的淳朴乡亲。尽管我的文笔比较拙劣,构思也并不精巧,可还是收获了大量的鼓励与点赞。因为,我所写的每一个文字,都蕴含了我对即将消逝的故乡最真切的爱。
如今,我的写作不再局限于我的故乡,我把笔触伸向更广远的视野,但《阳光下的蜀葵》仍然是我枕边常看的书。因为我知道,它不仅仅是那把帮我打开创作之门的金钥匙,也将永远是我徜徉在文学海洋里的摆渡之舟。
□李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