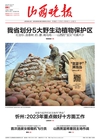父亲的坼地煨粪
记忆里,每年腊月开始,父亲便动手清扫圈室。他把羊圈、驴圈、猪圈、鸡圈乃至厕所里的粪土,提着䦆头使劲儿刨挖疏松后,用尖头铁锹把粪土从墙头的小孔里抛送出来,再用架子车推运至打麦场的路旁堆积着。
“人勤春来早。”即便是在春节期间,父亲也抽空扛着榔头、䦆头、铁锨把粪土堆翻晒一番。他一边翻一边用榔头砸碎土坷垃,粪土堆得仿佛一座毛茸茸的小山丘。正月十五后,父亲驱赶着小驴车,趁着土壤还冰冻着,沿着水沟或山路把粪土一车一车送至田间地头。连着十来天,父亲早出晚归忙碌着。
“二月二”后,土壤基本解冻了,父亲立即安排全家人开始坼地煨粪。天色微明,父亲早早地起床,催促妈妈和我们兄弟姊妹们赶快出发。
春寒料峭,冻风嗖嗖。一提一按,父亲把耙(一种农具)的扶手按入沙地(沙地是北方农村人工在土壤上面覆盖一层厚厚的红沙,用以保墒保水的土地种植模式),大哥、二哥和我拉着耙辕的把手,一耙一耙地把沙面翻起来。连续三四遍,直至耙下面的土壤完全裸露出来,才提着耙挪动位置继续坼地。等一垄沙地坼出地头后就搁下耙,用方头铁锨捡拾干净垄沟里土壤表皮的剩沙。换用圆头尖铁锨把土壤翻个身儿,并提着榔头砸碎土块,并且把土地整理平整。而后,就近抄些粪土散在土壤上面,再撒些化肥。若粪土不足,有时还掏挖些山洼里的浮土添凑。一垄沙地完成煨粪后,接着再进行下一垄的任务。
日上三竿,打开提包吃些馍馍喝点儿水,稍事休息。父亲絮叨着:“人养地,地养人。庄稼没粪,不如不种。人把地养好,地把人喂饱。人靠饭长,地靠粪养。”接着,继续忙活起来。
晌午时,天气炎热,牵起衣角揩揩汗水。劳作过程中,父亲就说起他的宏伟打算,比如哪块地种麦子、哪块地种西瓜、洋芋、玉米、高粱和糜谷,或着栽几株桃树。
傍晚时分,母亲先回家准备晚饭。父亲、哥姐们和我把一天耙过的沙塄摊平就算收工了。回头看看脚印整齐的沙地,有一种劳作的成就感。
夜幕降临,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家,坐在凳子上就不想站起来,直至吃过晚饭,立即上炕睡觉。头挨在枕头上,就啥也不知道了。
三四天的工夫,终于完成一块地的坼地煨粪工程后,“战场”迁移到另一块地里接续战斗。每年煨粪的主要是准备种植瓜果的田地。
精耕细作,三犁四耱。包产到户后,父亲种着十几亩地,从坼地煨粪、播种锄地到收割采摘,他把每块地弄得干干净净,从来不曾撂荒。
记忆中,八口人的田地平时父母和二姐做,其他兄弟姊妹们空闲时帮些忙。人多时,父亲是总指挥,有自己的主意,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安排得很清楚。父亲是一家之主,岂敢僭越违逆。父亲这种勤劳不辍的习惯,深深影响着我们兄弟姊妹们,我们从来不敢偷懒躲闲,总是设法尽力去帮衬些。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老家依然很穷,缺吃少喝,十年九旱,土壤贫瘠,且多为山坡地。全家老少的所有支出费用必须依靠土地的产出获得,贫瘠的土地寄托着父母全部的生活希望。一年四季,多年如是,父亲每天早出晚归,不知疲累地劳碌在田间地头,勉力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不至于遭受冻饿之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蒙眬中,微风一阵阵拂过,父亲的田地里枝繁叶茂,瓜果翠绿,香味飘飘。
□李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