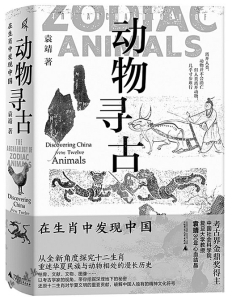一听就会入迷的十二生肖考古课,《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节选——
上古神灵和始祖为何是人首蛇身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
袁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经典体现。这十二种生肖动物中,除了龙是虚构的,其余均在考古遗址中有所发现。本书从动物考古学家的视角,分析各大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以及各种反映动物形象的青铜器、陶器、画像砖石、绘画,再结合相关的文字记载,还原了生肖动物的起源、驯化,以及它们在华夏民族生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仔细讲述了华夏民族与动物自新石器时代起,同行至今发生的种种有趣故事。该书作者袁靖是知名考古学家、考古学界金鼎奖得主。
蜥蜴类和蛇类是现存爬行动物中最兴盛的类群。这类动物的头骨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蛇类的表现尤其明显。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头部结构把它们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实际上,蛇类是从蜥蜴类演化而来的。在白垩纪(大约开始于距今1.45亿年)时期,最早的蛇开始出现。蛇是爬行动物中进化最快的类群,大多数现生蛇所在的科,是在中新世(距今约2300万年-533万年)才开始大量发展起来的。
迄今为止,发现蛇骨的考古遗址仅有紫荆遗址(位于陕西省商洛市)一处。这个遗址自下而上包含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龙山文化等4个文化层,年代自距今约7900年一直延续到距今约4200年。在3000多年里,属于不同文化的古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遗址中的那些蛇骨经过鉴定,属于爬行纲、有鳞目、蛇亚目、游蛇科,但属和种无法确定。游蛇科是蛇目中种属数量最多的一个科,有将近300属,约1400种,包括三分之二的现生蛇类。我国的游蛇科也有30多属,超过140种,广泛分布于全国。
考古遗址中很少发现蛇骨,这应该与考古遗址中很少发现鼠骨是同样的原因,即早先考古过程中没有开展水洗筛选工作,因而丢失了这些遗骨。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凡它之属皆从它。蛇,它或从虫。”许慎提到的“它”便指的是蛇。他指出,上古时期的人们害怕蛇,见面打招呼都要互相询问是否有看到蛇。这些文字反映了两个信息:一是古时蛇的数量不少,二是可能因为蛇无足而能行走,而且毒蛇还能毒死人,所以古人十分畏惧蛇。
20世纪60年代末,我从上海到云南西双版纳插队落户,在水田里、山路上多次见过一些小蛇,甚至在干农活时还被蛇咬过几次。这些小蛇身上的骨骼每块大多仅有几毫米,所以考古发掘出来的泥土如果不经过水洗筛选,肉眼确实难以辨别,因而没有发现古代蛇的遗骨也是很自然的事。
但我们根据文物上发现的蛇逼真的形象,以及古人对蛇的文字描述,可以推断出它们在古代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动物,所以古人能仔细地观察并准确地把握它们的特征,最后以艺术的形象展示出来。
甲骨文中的“蛇”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尤其是三角形的蛇头,蜿蜒扭曲的蛇身,都传神地描述了蛇的形态特征。从小篆开始,“蛇”字就有了些许现在“蛇”字的迹象,隶书则表现得更明显,到楷书才成为现在的“蛇”字。
在《诗经》里,蛇被视为吉祥的动物。《小雅·斯干》是一首祝贺周王新建的宫殿落成的诗歌,其中有“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虺”在古书中指的是一种毒蛇,这几句话的大致意思是,如果梦到熊、罴、虺和蛇,那就是即将生育儿女的吉兆。
古代文献典籍中关于蛇和蛇之意象的记载,最突出的应属上古时期神灵和人类始祖的人首蛇身形象。如汉画像石中人首蛇身状的伏羲和女娲(华夏始祖),事实上,不止是他们,在古代文献中,上古时期的神灵多是人首蛇身的模样。王仁湘考证古代文献,认为除了伏羲和女娲,其他三皇五帝,直到大禹,也几乎都是人首蛇身的模样。仅《山海经》便多次提及许多人首蛇身或操蛇、践蛇、珥蛇的神灵神人,例如女娲、伏羲、烛龙、延维、窫窳、共工、相繇、贰负神、黄帝、启、奢比尸以及众多山神。
有关操蛇之神的故事,我们更加耳熟能详的恐怕要数战国早期的作品《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典故。愚公因出行被太行和王屋两山所阻,发愿要把山搬走,自己搬不完就让后代继续搬,“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手执灵蛇的山神听说了,怕他们真的挖个不停,便报告给了天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荣曾指出,操蛇神怪的雕像或画像多出于河南南部、湖南、江苏等与战国时期楚文化相关的地区,这也证明了南方多蛇的观点。直至汉末时期,文学家王延寿在游览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建造的灵光殿时,看到殿中壁画而作《鲁灵光殿赋》,还提到“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可见在距当时将近300年的汉初,作为华夏始祖的伏羲与女娲就已经是人首蛇身的形象。
为什么上古时代的始祖和众多神灵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
这或许反映了上古时代人们盛行的图腾崇拜。蛇在我国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动物,从南到北的平原、沼泽、山地、丘陵、江河都可见其身影。古人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蛇,发现它们无足而能行走,毒蛇还能致人死命,自然而然地对这种神秘的生物产生了敬畏情绪,在观察到它们会冬眠和蜕皮等生活习性后,更延伸想象出它们具有长生不死和死而复生的神奇能力。古人的生存环境恶劣,生命往往受到大自然的威胁。他们希望自己能与这些神奇的生物有所联系,以获得它们的庇佑,帮助应对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于是他们把蛇想象成神,并按照蛇的特点来塑造始祖,始祖和神灵便成了人首蛇身、半人半兽的形象。
闻一多在《伏羲考》里生动地阐释了这个过程。他认为华夏民族的图腾是龙,而龙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都是蛇。一开始人是以蛇作为自己的祖先,极力把自己装扮得像龙(越人断发文身以像龙子),这是“人的拟兽化”。但无论如何装扮,都只能做到人首蛇身、半人半兽的地步,而不是全然的蛇。但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进步了,于是他们开始把始祖的形象设置成人首蛇身,这叫“兽的拟人化”。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过去模仿断发文身以像蛇的习俗被废弃,连记忆也淡薄了,于是始祖的模样就变作全人形了。
神灵和始祖的形象从兽到人兽同体再到全人形这个过程,究其原因,体现的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在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当大自然的威力远远大于人类之时,神灵和始祖的形象就是全兽形的;当人类发现自己有能力改变大自然之时,神灵和始祖的形象就变成了人兽同体;而当人对大自然的认知加深,改造力度和信心增强之时,神灵的形象开始转变为以人为主,人类开始以自己的形象来塑造始祖和神灵,但此时蛇仍然具有诸如蜕皮和冬眠(象征着死而复生和长生不老)等为害怕死亡的先民们所向往的特点,所以蛇虽然走下神坛,但没有消失,而是降格为部落首领的重要附属物,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