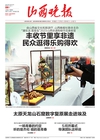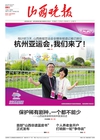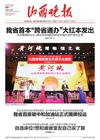一瓢乡愁
邻居家小院里种了棵葫芦,一根长长的藤蔓,牵着一群大大小小的“葫芦娃”煞是可爱。
千里之外的故乡,也曾吊挂着这样大大小小的葫芦。到了秋天,葫芦由青绿变成金黄,老去的葫芦掂在手里已没有了分量,母亲便左挑右选,找几个模样周正的,摘下来,对半剖开,挖去馕和籽,再风干几天,做成瓢,分给亲邻。
锅碗瓢盆,这里的瓢指的就是葫芦瓢,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瓢是日常生活的必备。那时候,有大瓢、小瓢,水瓢、面瓢,各种各样的瓢。
小时候,放了学在外面疯玩,追逐打闹,跑得一头大汗,渴了就“呼哧呼哧”地窜回家,拿起水瓢,从门后的大水缸里舀上半瓢水,“咕咚咕咚”灌下去,那感觉特别过瘾。身处孔孟之乡,后来上学读到《论语》里记述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竟因为和颜回过着同样的生活而沾沾自喜,箪食瓢饮过后,便会拿出书去认真学习,期待有一天成为书里的人。
要说小学时代最大的愿望,那便是生病了,生病后不仅可以请假不用上学,还能享受到特殊待遇。母亲每每见我茶饭不思,病恹恹的样子,便会拿起小面瓢,去面瓮挖上一小瓢面,切上点葱花,再打上俩鸡蛋,加点水,一搅和,倒在锅里用油一煎,香甜松软的鸡蛋饼就做好了。那时家里有大大小小三个瓢,大瓢舀水,小瓢挖面,还有一个盛粮食。母亲在小院里喂了几只鸡,每天都会喊小弟用瓢挖些玉米、高粱去喂鸡。小弟一边从瓢里抓玉米,一边嘴里发出声响,唤鸡过来。小鸡们啄食一会儿,便抬头看一眼小弟手中的瓢,那场景至今还浮现在脑海里。
母亲还曾多次讲过姥姥拿着小瓢去邻村讨饭的故事。母亲自幼聪慧,却生不逢时,整个青少年时期几乎都是在挨饿中度过的。姥姥、姥爷勒紧裤腰带,拼着老命供着家中这个“女秀才”读书。母亲说那时最怕过春天,青黄不接的日子,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在外地求学的她每次回家,姥姥都会拿着小瓢,提前去很远的外村讨饭。因为姥姥娘家亲戚多,姥姥怕让亲戚看到,总是要绕很远的路,才能讨上一小瓢地瓜面什么的回来……饿得两眼发花的母亲,总会如男孩子般爬到树上,去撸臭椿叶子,拌上点姥姥讨回来的地瓜面,放锅上煮了吃。
过年的时候,姥姥让母亲和面包几个饺子,母亲拿着面瓢从面缸底挖半天,才挖上半小瓢面,勉强包几个饺子,一人仅够分一两个。
后来,当母亲领着我们姐弟拿着一瓢大米、一瓢玉米去排队爆米花的时候,母亲说,总感觉那些大米、玉米都在笑,像一颗颗笑容背后的牙齿。
粮食,在挨过饿的母亲眼里,是多么珍贵的所在。这盛满瓢的粮食,可以喂饱她的孩子们,想着小瓢随时可以挖取的满缸的粮食,想着孩子们可以四野玩耍、满心的喜悦,母亲总是很满足。
几十年过去了,家里已经有了瓷的、塑料的、不锈钢的等各种器皿,但我家至今还保留着过去的那两个瓢。年代久远,老瓢却依然不减与生俱来的乡野气质,它金黄暗褐的色泽,与故乡泥土的颜色并无二致,也与乡间生灵老去的面容相同,布满苍茫、斑驳的时光印痕。老瓢上面有母亲用线缝过的痕迹。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当年缝老瓢的情景,她用锥子先在裂缝的两边扎上对衬的小孔,再拿大号针穿上线,最后耐着性子,一针针地缝起来。
远远地,我好像嗅到了老瓢散发出的气息,夹杂着泥土与草木的芳香。老瓢还在,母亲却走了。叶落归根,人终归还是要回到养育他的泥土里,而老瓢张着大嘴,召唤着远离故乡的人们,变成了一瓢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葛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