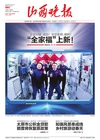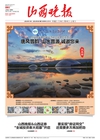乡音 流动的乡愁
屈指一算,离开老家40多年了,听见乡音倍感亲切。乡音难忘,让我魂牵梦绕。
古诗中写到“乡音未改鬓毛衰”,每次回到故乡,我都用有些拗口生疏的乡音,给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熟悉的长者发烟,用曾经熟悉的乡音和婶婶、大娘们满脸笑意地问好,以示我没有忘本。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同时,一个人一旦学会了乡音,终其一生都不会忘记,它根植于血液中,追随我们一生。
我童年的闽南语系里:“屋”称“厝”,“筷子”称“箸”,午饭叫“吃昼”,眼泪叫“眼屎”……这些有趣的称呼根植于我们的血脉中。
长大一点,常听母亲唠叨那些闽南气候歌诀,到哪个季节母亲就对哪句“歌”,打小在农家长大的我听惯了这样的“哼哼歌”,并偷偷验证它们的真实性。听着听着,自己也俨然成了“气象小专家”。“春分秋分,瞑日平分”“五月菜豆雨,六月火烧埔,七月水流芋”“六月立秋紧丢丢,七月立秋秋后辣”“大寒不寒,人马不安”“冬日大雾罩勿开,戴笠披棕蓑”。奶奶不识字,她用这些带着家乡口音的土谚播种四季。
乡音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胎记。我父亲打上世纪60年代初背井离乡,至今已经六十年,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成了耄耋老人,但老家的口音始终未变。
老家福建乡音里有着大量夹杂运用“屎尿屁”的成果,虽然不雅,却十分生动、精炼、活泼。平时弟弟因事情太多了,手忙脚乱应付不过来,父亲会说一声“拉屎被屁误”。话里有同情有安慰有激愤也有不屑,全看彼时彼地彼场景,需妥善运用灵活理解。向老友吐槽某人的一大堆劣迹,父亲会从牙缝里轻轻地挤出两个字:“屎人!”那一刻这俩字真是渊深如海,包含了最广泛的共识,啥也别再说了,一切尽在其中。
乡音还是流动的乡愁,眷恋一生。还记得母亲在世的时候,每次给福建老家的亲人打电话,都是用乡音,我一句也听不懂。母亲每一次念家念亲人的时候,拿起电话,痛痛快快地说一通,是慰藉思乡情最好的方法。所以啊,乡音也像黏合剂,黏住了天各一方的亲情和思念,说着浓浓的乡音,月亮都显得圆了许多。
每一种乡音更像是每一个故乡的专属歌谣,每个故乡的乡音都有它独特的调调,我们每个人从说话起就耳熟能详,不用费劲去教就会。我们不管走多远,只要听到那个调调就能触动我们心底的那根弦,甚至会热泪盈眶。
没有乡音的地方该是多么的了无生趣啊!走过四面八方后才知道,有自己熟悉乡音的地方才有家的感觉,才有浓浓的亲情围绕。想家了,一张口乡音流出来,就像被母亲呼唤着乳名,顷刻间泪流满面,故乡的人和事也从记忆中袅袅走来!
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乡音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那高低起伏的各地乡音,流淌的都是原汁原味的乡愁。
□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