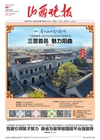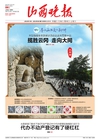边大绶“虎口余生”
边大绶,字素一,号长白,直隶任邱(今河北任丘县)人。明崇祯举人,官陕西米脂知县。入清后,补河南修武知县。顺治八年(1651),升太原知府。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朱衣道人案”案发时,曾设法为傅山开脱。傅山无罪获释,魏一鳌证词是为根本,但边大绶与孙茂兰、龚鼎孳、曹溶等从中周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边大绶与傅山多有交往,直到顺治十三年(1656)边氏以病告归。傅山在《致戴枫仲札》中曾这样记述:“前月杪出门,拟自汾过府,展积冲寒,入宁乡。不谓遂稽世评,日出山则。边府尊有信将发,督以文事,匆匆北矣。”也正因与傅山的交往,边大绶为晋人所熟知。边大绶曾为明臣,后为清吏,但不仅没有被南明如龚鼎孳等视为“从贼者”,也未被清廷像龚鼎孳、曹溶等列入“贰臣”,是一个较为特别的存在。
在康熙十一年(1672)、乾隆三十六年(1771)与光绪八年(1882)三版《寿阳县志》艺文中,均收录有边大绶《过方山题》诗:“三十年来岁月虚,偶因烽火过禅庐。白云不断人行路,消受松风一夜余。”而在光绪八年(1882)《寿阳县志》“卷十二·艺文”中对边大绶是诗还有如下释解:“《虎口余生记》。边大绶,任邱人,明末为米脂令,曾奉密旨掘自成祖墓。燕京破后,吏捕大绶以献,途遇卜者曰:君勿忧也,遇三阳而自开。及闯贼败西走,械大绶至寿之朝阳阁。外守稍懈,大绶遂乘间遁去,时正九月重九日也。夜匿方山,题一绝于寺壁,伺贼去,乃觅路归。”这也是所谓“三阳开泰”的传说。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传说背后也并非没有历史的影子。崇祯皇帝继位时的明王朝,早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政治上党派争斗,社会上叛乱不止,经济上危机重重。尽管崇祯皇帝试图励精图治,登基不久即向阉党开刀,逼死魏忠贤、崔呈秀,并在两个月后磔尸剖腹,将首级分别悬挂在其各自家乡以警告同党。还对魏忠贤党羽展开清洗,二十余人被处死或被迫自杀。其中包括客氏及其兄弟、儿子,乃至魏忠贤从子,被充军、戍边、削籍或其他惩处甚多。同时还对魏忠贤弄权时致死或受迫害人员家属公开表示关切,或封赠抚恤。崇祯皇帝也竭力使其政权免受任何派别控制,但阉党与东林党人盘根错节,已难以彻底免于党争之祸,又不得不在东林党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寻求平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期间叠加了中北部罕见的干旱,东北地区新崛起的少数民族军事联盟借机入侵,西北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揭竿而起,朝廷既剿亦抚,却始终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局势得到控制又反复恶化的局面交替出现。由此朝廷在不得不减少不必要开支的同时,一而再增加赋税,而且许多捐税要以白银支付,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在如此危机四伏时刻,崇祯皇帝先后诛总督七人,巡抚被戮者十一人。时任陕西总督军门汪乔年、米脂县令边大绶则是一通“神操作”,共商所谓奇计,由边大绶访诸米脂乡野,探得李自成祖、父墓地后,发其冢,剖其棺,灰其骸,断其龙脉,以助剿灭。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初八日,在寻访到李自成祖父营葬知情人后,边大绶随唤练总黑光正、堡长官王道正率领箭首三十名,乡夫六十名,冒雪前往。山路陡滑,行马不成步行,鸟道崎岖攀援,一昼夜行二百余里。过李自成村庄山后,抵达山势环抱,气概雄奇,林木丛杂的一片大小二十三座墓冢,伐五六冢未见营葬黑碗,遂宿李自成旧窑。第二天再掘数冢,掘得李自成祖李海、父李守忠墓。边大绶如此向总督军门汪乔年塘报:“再掘数冢而黑碗见,即李海墓也。骨黑如墨,额生白毛六七寸许。其左侧稍下一冢是李守忠墓。顶有长榆树一株,其粗如臂。用斧斩之,榆断墓开。中盘白蛇一条,长一尺二寸,头角崭然。随取装入黑光正顺袋中。伐其骨骸,凡骨节间,皆绿如铜青,生黄毛五六寸许;其余骨骸有毛者七八冢,尽数伐掘,聚火烧化。大小林木千余株,悉行斫伐,断其山脉。贼墓已破,王气已泄,贼势当自败矣!其黑碗、白蛇,呈验军门,理合登报。”而汪乔年回札:“接来札,知闯墓已伐,可以制贼死命,他日成功,定首叙以酬!草覆。”最后的结果是,李自成不仅没有因此遭灭顶之灾,反而势如破竹攻下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但早在崇祯壬午(1642)春,边大绶伐李自成族墓后不久,义军行牌已至西安,米脂姻亲同党制造舆论,群谋里应外合,将边大绶、黑光正等献于义军。边大绶密禀按台沉搁,惶惶不可终日。幸在崇祯癸未(1643)大计,新任按台与抚台相左,抚台大力举荐,按台则一味打压,边大绶终遭降处。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抚台按台均谕留候题,边大绶力辞解任。
七月初旬,边大绶往山西泽州投奔州守长兄边大顺,十月六日义军破潼关,陷西安,州县望风投献,遂于十一月回归任邱。崇祯十七年(1644)初,义军直逼晋东,固关失守,三月二十一日攻下京城,建立大顺政权。边大绶杜门谢客,听天由命。但仅一个多月后的四月二十八日,吴三桂降清。边大绶于次日被大顺县府收押,交于白、吴二钦差押解西行。经肃宁、安平、无极、真定、获鹿、固关、平定,五月十一日天亮行至寿阳南关,已是人困马乏,饥饿难耐。边大绶乘看押仰卧酣睡,独门北行回返,以取水为由,敷衍众人,从临河房屋后门跳至无水河道,循城北行。遭遇盘问者,索财后放行,仅存蔽体之衣,向东北逃去。期间曾潜身山畔土窑躲避,六七次遭骑兵搜寻。夜深人静后,借月光逃去。幸遇善人指路,行三十余里入方山寺脱险。栖身寺中六日后,经小路逃离,直到五月二十五日回到任邱。这一惊险经历,边大绶于顺治元年(1644)仲秋既望自传为《虎口余生记》刻版。文中如此感叹:“呜呼!是役也,始则入虎穴,探虎子,继而履虎尾,捋虎须,盖几不免于虎口矣!乃卒不受其咥,以脱于难。吁!岂非天哉!”
话题至此,似乎已无必要赘述。地方志书中所录边大绶《过方山题》诗真实反映了边大绶“虎口余生”的经历与感受,但光绪《寿阳县志》中所谓“途遇卜者曰:君勿忧也,遇三阳而自开”的记述,则纯属好事者虚传,与事实不符。寿阳城东关有朝阳阁,邑人陈完于明正德丁丑(1517)间创建,为寿阳一方形胜,边大绶确也途径寿阳东关朝阳阁后脱逃,但时在四月十一,而非九月初九,自然也无所谓“三阳开泰”之说。
□郝岳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