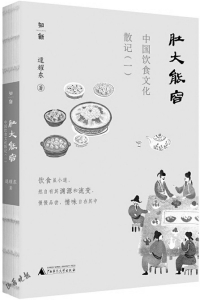将油盐柴米酱醋茶提升到文化层面,《肚大能容:中国饮食文化散记》节选——
凉拌海参与《随园食单》
《肚大能容:中国饮食文化散记》 逯耀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书是一部随笔集,汇集了台湾历史学家、美食家逯耀东先生创作的有关中国传统饮食文章若干篇。作者结合历史文化考察和自身探索美食的经历,在描写这些佳肴的制作和味道的同时,注重追寻美食背后的文化和美食的形成与流变,将油盐柴米酱醋茶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将饮食、生活、文学、文化、历史融合,借学养之力,追求大羹玄酒最深醇的至味。不只停留在“吃”的层面,更是在探索中国人的“吃”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
海参入馔,由来已久。三国时,吴国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称海参为土肉:“土肉,正黑,如小儿臂大,长五寸,中有腹,无口目,有三十足,炙食。”元贾铭《饮食须知》分析海参,认为其:“味甘咸,性寒滑。患泄泻痢下者勿食。”谢肇淛《五杂俎》叙海参之形状及其性:“海参,辽东海滨有之,一名海男子。其状如男子势然,淡菜之对也。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初海参多为药用,明清之际的《本草从新》《百草镜》有记载。《百草镜》谓以海参,充庖熩猪肉,食可健脾。《闽小记》则说:“海参得名,亦以能温补也。”因海参性温,与鱼翅并为宫廷御食。《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载:“海参,鳆鱼,鲨鱼筋(鱼翅),肥鸡,猪蹄筋,共烩一处,名曰三事,恒喜用焉。”
入清以后,对海参的记载渐多。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对海参的生长环境、加工的方法皆有叙述,并谓海参“至伏月则潜伏海中极深处石底,或泥穴中,不易取,其质肥厚,皮刺光泽,味最美,此为第一,名曰伏皮,价颇昂,入药以此种为上”。郝懿行《记海错》则谓“海人没水底取之,置烈日中,濡柔如欲消尽,瀹以盐则定,然味仍不咸,用炭灰腌之,即坚韧而黑”,其腌制之法与今同。至于海参入馔,袁枚《随园食单·海鲜》有“海参三法”:
海参,无味之物,多沙气腥,最难讨好。然天性浓重,断不可以清汤煨也。须检小刺参,先泡去沙泥,用肉汤滚泡三次,然后以鸡、肉两汁红煨极烂。辅佐则用香蕈、木耳,以其色黑相似也。大抵明日请客,则先一日要煨,海参才烂。尝见钱观察家,夏日用芥末、鸡汁拌海参丝,甚佳。或切小碎丁,用笋丁、香蕈丁入鸡汤煨作羹。蒋侍郎家用豆腐皮、鸡腿、蘑菇煨海参,亦佳。
《随园食单》所列的海参三法,一为煨焖,一为作羹,一为凉拌。其凉拌“夏日用芥末、鸡汁拌海参丝”,梁实秋凉拌海参的灵感,或得自此。凉拌海参一味,亦售于食肆,《桐桥倚棹录》记载道光年间苏州虎丘桐桥间的食肆,出售的众多菜中,有烩海参、什锦海参、蝴蝶海参、海参鸡、拌海参等多种。其拌海参或与《随园食单》同,已成为市井流行的佳肴。
随园主人袁枚,清乾隆四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前后历任江苏潥水、江宁知县。年未四十即退官,于南京小仓山筑随园,或谓随园所在,即曹雪芹家的旧府第。自此隐影山林,广交宾朋,论文赋诗五十年,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与诗人。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多种。《随园食单》是袁枚四十年饮馔经验的集结。《随园食单》序云:“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每在外得佳肴,即命家厨前往执弟子礼学习。因此“四十年来,颇集众美”。《随园食单》刊于乾隆五十七年,反映了清康乾盛世的江南饮馔风貌。
袁枚在《随园食单》序中批评了孟子的饮食观念,他说:“孟子虽贱饮食之人,而又言饥渴未能得饮食之正。”这种批评不仅突破以往饮馔之书,著录于“农家”“方技”的框限,并将饮馔之书提升至艺术的层面。《四库总目提要》即将饮馔之书,自“农家”与“方技”析出,与器物、墨砚、花卉并列,置于“艺术”之后,另成“谱录”一类。负责主编《四库总目》的纪昀与袁枚同时,《随园食单》更实践了这种观念,并引导明清文人食谱更上层楼,进入一个新的境界。饮食虽为小道,但袁枚认为也是一种学问。他说:“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
《随园食单》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江鲜单”“特牲单”“杂牲单”“羽族单”“小菜单”“点心单”“茶酒单”等十四种,三百余品。对于各种材料的处理,一如其写诗论文,特别重视性灵。所以他说:“凡物各有先天,如人各有资禀。人性下愚,虽孔孟教之,无益也;物性不良,虽易牙烹之,亦无味也。”中国饮馔之书可分三类:一为叙烹调之,如北魏崔浩《食经》;一为仅载菜肴品目,如唐韦巨源《烧尾宴食单》;一为叙饮馔掌故,如宋陶谷《清异录》。袁枚《随园食单》叙烹调之法,仅举大端。但举一反三,并参照扬州盐商童岳荐的《调鼎集》,仍有迹可循。此后的淮扬菜系即由此出,也是京苏大菜的渊源所自。
犹忆十多年前,初访金陵,寓于南京大学,得识其餐厅的莫师傅。莫师傅是餐厅外包的老板,特一级厨师。或出自胡长龄门下。胡长龄是金陵的首厨,能治随园菜。几次餐叙都是由莫师傅掌勺,吃到地道的金陵美肴。于是和他谈到随园菜。当时刚开放不久,他说材料不易取。的确,后来我临行,回请接待的诸先生,请莫师傅治一席。席间有冬瓜盅一味,所用的冬瓜,还是莫师傅亲自下乡自个体户家中搜得。因为当时市上所售冬瓜,既大且老不堪用。后来经济渐醒,发展观光,各地纷纷出现仿古菜,杭州有八卦楼的仿宋菜,西安有曲江宴,红楼、金瓶饮馔也流行起来,南京的随园宴也应运而生。我虽皆未尝其味,但观其图片及文字记载,多华而不实,难见神韵。
不久前,饮食文学研讨会在台北召开,于圆山饭店摆过一次随园宴。不知谁拟的菜单,是日菜肴多不见于《随园食单》。可考者仅虾饼,按《随园食单·水族无鳞单》“虾饼”条下:“以虾捶烂,团而煎之,即为虾饼。”夏曾传《随园食单补证》:“或以网油卷而灼之,即为虾卷。”是日金钱虾饼颇类粤菜的桂林虾丸,是油炸而非“团而煎之”。
另有小菜大头菜一碟。《随园食单·小菜单》有大头菜一味,仅云:“大头菜出南京承恩寺,愈陈愈佳。入荤菜中,最能发鲜。”台湾所制大头菜,过咸而不香。须入水浸泡半日,始可食用。承恩寺的大头菜已不可得,扬州三和酱园的大头菜仍可用。不过夏曾传《随园食单补证》,引《云南记》叙云南大头菜,谓“嶲州界缘山野间,有菜大叶而粗茎,其根若大萝卜。土人蒸煮其根叶而食之,可以疗饥,名之为诸葛菜”,因诸葛亮南征时,军士曾以此菜充粮,故名。诸葛菜之根腌制后即为云南大头菜,夏曾传以此补注《随园食单》大头菜,云南大头菜或与承恩寺大头菜味相近。
前时去香港,在街边南货店货架底层,搜得云南玫瑰大头菜两盒。归来,忆起《食单》所谓大头菜“入荤菜中,最能发鲜”。于是,试依《食单》所载炒肉丝之方,略以调配,成大头菜炒鸡丝一味。按《食单》所载炒肉丝:“切细丝,去筋襻、皮、骨,用清酱、酒郁片时,用菜油熬起,白烟变青烟后,下肉炒匀,不停手,加蒸粉,醋一滴,糖一撮,葱白、韭蒜之类。”以肉丝换鸡的里脊丝,以云南大头菜,配阿里山发妥的冬笋尖,红椒一朵,并切细丝。依《食单》之法烹调之,出锅之后鸡丝与大头菜黑白分明,并衬以笋尖的微黄,椒丝的润红,色彩鲜艳,鲜味尽出,配粥下饭,夹馒头或酌酒,皆宜,置于冰箱亦可冷食。所以一粥一饭一肴,当思来处不易。而且皆有渊源,虽有变化,但不离其宗,不是凭空臆想的。
那日随园宴,我也应邀敬陪末座,席间要我说几句话,我仅说随园之食,宜小锅小灶。是日席开十余桌,热闹喧哗非凡,但已无人想到袁枚《随园食单》的雅致了。袁枚视其《食单》与诗作等同,其《杂书十一绝句》咏《食单》云:“吟咏余闲著《食单》,精微乃当咏诗看。出门事事都如意,只有餐盘合口难。”不难体会袁枚《食单》所蕴的诗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