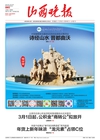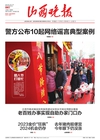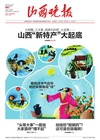流淌在血液里的乡间年味
元旦过后,城里便到处充满了要过年的味道。家政服务的小卡片开始到处飞,微信里冷不丁就推送过来一则购买年货的小广告,进出小区的快递小哥比平时多了些趟次,喜滋滋地把满满当当的年货送到居民手里,商超里客流平缓的态势也完全被涌动的人流取代,服装、鞋袜、金银饰品、灯笼、对联前挤满了精心挑选的人们……而当真到过年时,城里反倒安静了许多。整夜里响不停的鞭炮声没有了,奔波一年的新老城市人也携家带口早早地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有点钱财有点闲暇者也趁早飞往温暖的地方,喧闹的城顷刻变得空旷了起来。除了门口贴满的红对联,以及扎堆在公园、影院、饭桌旁的人流,与平日差别无多,城里的年慢慢变得索然无味起来。
乡村的年味自然来得要晚,但较之城里,味道更浓烈,持续的时间也久。过完了腊八节,年的序幕才算徐徐拉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推年磨、做针线活是最具年味的苦活计。过年的吃食只能依靠老祖宗留下的石磨,常常天还不亮,各家院子里的大人们便将麻绳系在磨杆前边拉起来,女人和孩子们则在后边推,凛冽的寒风中传来“嗡嗡嗡”的声音,在静谧的夜空中仿佛一首命运的交响曲。
那时的家庭人口都多,再加上待客,正月里又有不敢动磨的讲究,常常要准备下一个多月吃的白面、豆面、玉米面、高粱面。白面是极少的,能磨上三二十斤小麦的绝对算是村里的上等人家,普通家庭磨的多是玉米面高粱面,而最难磨最费力气的当数玉米面。玉米颗粒大,要先磨两三遍将其磨碎成小颗粒,然后才能再磨成面。磨面的过程中小颗粒也坚硬无比,没有三遍五遍不能成为细细的面粉。所以磨玉米往往被放在推年磨的最后,全家老幼齐上阵,攻坚克难。后来村里有了粉碎机,磨玉米便不再是心中的负担。
那时,大人小孩过年的穿着全靠母亲们的双手,衣服要靠手去缝,鞋袜要靠手去做,为了赶上过年穿用,她们在昏黄的油灯下熬走一个又一个黎明。最苦最累的是纳鞋底,那用浆糊一层一层粘了十几层厚的鞋底,需要一针一针带着麻线穿过去,一只成年男人的鞋底,少说也有四五百个回合,尽管有简易的辅助工具,但一只鞋底纳下来,手背上会出现好几条沟壑,有时还泛着血丝,但不能有丝毫的闲暇,马上换只手进入下一只鞋底。母亲们就这样忍着痛来回倒替着,为着是让全家人在大年初一早晨都穿上一双崭新的土工布鞋。
对于孩子们来说,年味莫过于穿上新衣裳,揣上几个鞭炮相跟着去挨家挨户串门拜年。年三十的晚上,等他们熟睡后,母亲便将新衣服、新鞋袜,还有两毛的压岁钱齐齐整整地放到炕沿边孩子们的枕头旁。即使是最爱睡懒觉的孩子,在大炮小炮的噼噼啪啪声中都会早早地从炕上爬起来,在反复嘱托大年初一不敢说不吉利的话音中,便不顾严寒相约几个小伙伴而去。最先要到的地方是去寻找没有响过的鞭炮,在放过的爆竹碎末中挨家挨户扒拉,总能捡到不少,然后放进衣兜,到谁家院子里,往火炉子里扔一个,“啪”的一声,就知道有人拜年来了,主人便掀起门帘,将一帮毛头孩子让进去,然后拿出酒枣和自己炸的油果子让吃。在有人在外边工作的几家,偶尔还能得到个水果糖,真是如获至宝,宁可让其受热黏在衣兜里也舍不得拿出来吃。大年初二三,村里的大秧歌出场,劳作了一年的人们在锣鼓唢呐声中扭起来,尽情地抒发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有文化的伞头总能即兴编唱出吉祥喜庆的秧歌,让人们在捧腹中津津乐道。随着闹上七天八天的大秧歌谢幕,年味也便渐渐地淡了下去,生活也恢复了常态。
当人们开始不再为衣食发愁的时候,乡村的年味也发生着悄然的改变。虽然在城里打拼的年轻人有的已娶妻生子,在电话那头一股劲讲什么都不需要准备,到时全家回来吃几顿饭、睡几晚上年就算过完了,但老人们总想着把年味传承给儿孙辈。他们说城里卖的油茶太腻,便用碾盘将自己种的小米碾成米面,然后放进少许的羊油,支起柴火炒出黄澄澄的油茶面,让孩子们能够喝出年味。又说拌凉菜用的芥末油还是自家熏的味道劲儿大,便将夏天收获的胡芥碾成芥末面,等着过年时用。女人们早已不再纳鞋底缝衣服,但总也闲不住的忙着为孩子们做着各种图案的鞋垫,在她们看来,城里一两块钱一双的鞋垫不舒服,所以每年都要为回家过年的孩子们准备上两双。
年三十晚上最具传统年味特色的垒火炉子自然是必须的项目,提前准备好百十斤上乘的块煤,单等到时在院子里将火炉烧得旺旺的,而这的确是孩子们的最爱。自从通上了电,煤的价格也飞涨,过惯苦日子的乡下人便将年三十家家户户垒火炉子的习俗改为院子里拉上一个电灯泡,但只要有子女从外地回来过年,火炉子是必须要垒的。除夕晚上只要看到谁家院子里点着火炉子,人们马上会说人家的孩子们过年回来了,而那些孩子们没有回家过年的老人,只能在睡觉前黯然地拉下电灯的开关。后来我常常想,乡下的年味,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人气,是烟火味。人少了,乡村的年味也会越来越淡,会渐渐失去传承和吸引力。
年前,深知我恋旧的兄长要寄来他自己制作的烧肉丸子和甜甜的酒枣,村里的发小们也会给我发些充满年味的短视频。每年正月,我也要带着孩子回去祭祖,有时扭几步大秧歌,顺便找寻着儿时的年味。虽然今年有些特别,孩子们有的忙着照看小孙孙,有的远渡重洋去做访问学者,但我和爱人一定还会回去的,在我们这代人心里,乡间年味早已流淌在血液里,而下一代,我想自然也会有他们对年味特殊的记忆方式。
□薛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