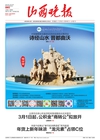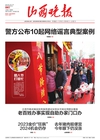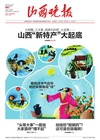一个“丑小鸭”乡村的华丽变形记,《花灯调》节选——
向家明初入高远村
《花灯调》刘庆邦著 作家出版社
该作是著名作家刘庆邦的长篇新作,呈现了一段“白天鹅书记”的下乡“探险”历程、“丑小鸭乡村”的蜕变传奇。
她已经拥有了令人艳羡的工作、美满幸福的家庭、富足安定的生活。在检察院跟高远村之间,她选择了后者,她走在田间地头、攀在悬崖峭壁、宿在简陋屋舍,在泥泞跟严峻中拓荒,在沟壑跟淤堵中楫水。从“走新路”到“闯新路”再到“致富路”,她的真心、良心、责任心付诸实际行动,让人民放心、舒心、开心,与广大村民齐心协力,共同书写了高远村这个“丑小鸭”乡村的华丽变形记。
春三月,山沟里的杏花开了,山顶还是寒凝冰封。那些杏树不是人种,都是鸟种;不是家生,都是野生。春来开花,不是谁让它们开的,它们自己觉得可以开,就自然地开了。它们开花,也不是为了给哪个看,不管有没有人看,它们只管开,白天开了,夜里接着开。淡淡的花香在山间弥漫,苦吟吟的、甜丝丝的。正是这样的杏花,让人一见,就喜得发惊。山顶的竹子在冬天也不落叶,似乎一直在带叶修行。虽说竹子的叶子一年四季都是绿的,可在冬天和春天有所不同。冬天的竹叶是燥色,一点儿都不明亮。到了春天,地气上升,春风一吹,叶片才一点一点变得明亮起来。一群麻雀飞进了一片竹林,它们嘴尖舌快,嘁嘁喳喳,在争相发言。它们像是就某一个问题发起了争论,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又像是并没有预设的讨论主题,自说自话而已。不知它们遇到了什么新的情况,大家一哄从树林里飞走了,集体飞向另外的地方。
据历史记载,十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海里只有波浪和鱼龙。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的起伏、颠覆和切割,海水退去了,这里变成了十万大山。海水没有了,但天上下雨地上流,水还是有的,只是水的形态变成了河流和湖泊。别看水是软的,山是硬的,天长了,日久了,水流却可以改变山岩,使有的山变高,有的山变低;在有的山上开了门,有的山上开了窗。河山相连,山水相依。水可以改变山,同时也可以塑造山。这儿的山里有一个溶洞,洞顶有一滴水珠,水珠以亘古不变的均匀速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向下滴落,几万年下来,竟在洞底的地上形成一座拔地而起、体高数尺的石塔。有道是水滴石穿,这里正相反,是水滴石长。因水里含有碳酸钙,久而久之,碳酸钙积累下来,就长成了琉璃宝塔样的钟乳石。看到这样的奇特地貌,在不可思议之余,人们往往会想到鬼,想到神,说是鬼斧神工。其实这跟鬼神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自然的造化、时间的作用,自然就是鬼神,时间就是神鬼。
这天一大早,向家明从市里乘车,往一个叫高远村的山村赶。车是向家明所在单位的一辆公用越野车,车的一侧书有红色的“人民检察院”字样,车顶安有警灯。这是检察院的领导特意给向家明派的一辆专车。向家明的职务只是检察院的一个科长,按说下乡时她还没资格坐专车。领导之所以破例安排一辆送她去高远村,一是对她下一步的工作抱有期望,二是去高远村山高路远,山路崎崎岖岖,去一趟不容易。
一年前的2015年春天,向家明正在检察员和公诉人的位置上干得好好的,被临时抓差补缺,派到一个贫困村当驻村第一书记。她没有辜负领导和大家的期望,一进村就开足马力,干得马不停蹄。她充分利用自己在市里工作的资源优势,很快把上上下下的脱贫攻坚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在上级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协助下,经过全村村民的共同奋斗,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全村的人均收入就达到了国家规定的脱贫标准,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当年年底,向家明被评为市里的优秀共产党员和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既然完成了驻村帮助脱贫的使命,按照市里关于驻村轮岗的规定,向家明可以理所当然地回到检察院,穿上板正的检察制服,继续做庄严的检察工作,并可以天天回家,过方便而优越的城市生活。然而就在这时,高远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因事回城去了,急需另派一个人接替第一书记的工作。检察院的领导考虑到向家明在驻村工作中成绩优异,并积累了脱贫工作的经验,就征求她的意见,希望她能去高远村当第一书记。向家明说,既然党组织这么信任她,那她去吧。征求向家明意见的是检察院的党组书记,书记说:你驻村刚回来,院里本不该再派你去驻村。可院党组在全院党员中挑来挑去,还是觉得你去当第一书记最合适。我们这样做有些鞭打快牛,对你来说可能有些不公平。我的意见是,你不必马上答应,先去高远村看一看,回头咱们再商量。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去,院里不会勉强你。书记提醒向家明说:高远村是咱们全省为数不多的深度贫困村之一,我去那个村看过。在去之前,我不太理解什么叫深度贫困,不知道深度是深到什么程度。去高远村看过才知道了,那个村的贫困是谷底的贫困、探底的贫困,是贫困到不能再贫困。高远村脱贫攻坚的艰难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向家明同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说到这里,书记见向家明面色有些凝重,微笑了一下,问:你不会被我的话吓着吧?
向家明说:不会的。我害怕老鼠,不害怕贫困。
为向家明开车的是一位有着多年在山区驾驶经验的师傅。上车后,向家明问师傅以前去没去过高远村,师傅说去过。向家明问,从市里到高远村有多远,师傅说,直线距离大约六十多公里。向家明乐观地说:不算太远,这个距离估计两个多钟头就跑到了。师傅摇头,说不行,保守估计也得跑四个多钟头。向家明问为什么,师傅说因为去高远村没有路。师傅的回答让向家明觉得有些可笑,她说:鱼在水中游,车在路上跑。没有水,鱼就不能游;没有路,车在哪里跑呢?师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高远村与山外不通公路,连简易的硬化路都没有,都是一些原始性的砂石路。在这样的路上,车像老牛爬坡一样,根本跑不起来。
进了山向家明就感受到了,师傅说得不错。砂石路坑坑洼洼,布满滑沙和坚硬的石子,车轮碾在上面,一弹一跳,像猴子玩杂技,一点儿都不踏实。山路弯弯曲曲,弯子多得数不胜数。人说羊肠子的弯弯多,这里的弯弯恐怕比羊肠子的弯弯还多。车子刚转过一个弯,以为该走一段直路了,不料又一个弯道马上出现在眼前。向家明听说过,这里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今日走在山道上,她有了新的体会,觉得应该在前两句评价的后面再加上一句,叫道无三尺直。路上弯道多,车子只能随着弯道拐来拐去,甩来甩去,向家明觉得自己的头都被甩晕了。山里海拔落差很大,低的地方有几百米,高的地方恐怕超过了两千米。车子跟着海拔的落差起起伏伏,山路“下海”,车子也得往“海里”扎;山路入云,车子也得使劲儿往高处拔。有一段路一路下坡,向家明眼看着车窗外有了农舍、炊烟、水塘、竹园和鸭子,以为车子总算开到了人间,离高远村应该不远了。可司机师傅却没有任何停车的意思,一踩油门,又向高处爬去。爬到又一个山顶,向家明偶尔往下一看,见刚才走过的路变成了一道时隐时现的灰线。山道还非常狭窄,对面走过来一头牛和一个拿着树枝放牛的人,车就得停下来,等牛和人走过去,车子才能继续往前开。如此逼仄的小道,还常常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万丈深渊,真乃处处危险、步步惊心。当一个农妇领着三只山羊并背着一背篓青草走过来时,师傅又不得不把车子停了下来。趁车子停下来时,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向家明解开安全带对师傅说,她到后面的座位上去坐。在师傅开着车时,她见师傅的两只眼瞪得像铃铛一样,开车开得全神贯注,她一句话都不敢跟他说。趁车子停下来的工夫,她才提出到后面坐。坐在前面时,面对道道深渊,她老是心惊肉跳,担心车子会一头栽进深渊里去。坐在后排座,用师傅的驾驶座位挡住她的视线,虽说有掩耳盗铃之嫌,但恐惧总算减轻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