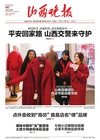正月里来“出门子”
经年陈事落成雪,雪携春风迎客来。
烟火年年,辞兔接龙,转而又到“出门子”时。我们这里将走亲戚唤作“出门子”,带着当地浓浓的乡土气息。
小时候,过年过得是一大段美好时光。物质并不富裕的年代,大家平日节衣俭食,但节后走亲戚绝不含糊。那时的人,贼热情、穷大方、好面子,自家不舍得吃的好东西,一股脑儿地打点包裹,留给“出门子”用。“出门子”的时长绵延续续,自初二至元宵,不是走亲戚,就是在走亲戚的路上。
老家正月“出门子”的仪式很讲究。老一辈有言,“出门子”要趁早,别怠慢,否则遭怪罪,而且出门分先后,认真也讲究,尽量别乱套。初一不“出门”,初二看丈人,重量级的亲戚走完了,才是后面的“先走姑,后走姨,姐姐妹妹凑一桌,表叔表舅靠后面”。
一年接一年,年年有好饭。走亲戚不能断,如果猛然断下一年,对方会很不高兴,认为是瞧不起人,隔年再去,难免被数落一番。如果三五年不走动,亲戚关系基本上就凉了黄花菜。
对大人们来说,一方面“出门子”时可以吃菜喝酒,更重要的是拥有了一次难得的亲近和沟通机会。小时候,交通不便,平时又忙,除了婚丧嫁娶、上梁盖房,亲戚之间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面。农家人充分利用节后这段农闲时光,串个门、唠唠嗑,谈古论今,把酒话桑麻,相互了解一下农事和信息:今年收成如何?来年打算种什么?听说供销社老李是你们村的,能不能给搞张缝纫机票……
酒足饭饱,已是日落西山。两条饼干、几个馒头在推推搡搡中,从包中拿出又装进,知道彼此不宽裕,是稀罕东西,自然相互谦辞推让。
当然,那时“出门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介绍对象,媒人也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尽力促成姻缘。旧时农村封闭,没网络,没交流平台,大姑娘、小伙子的活动范围有限,通过走亲串门,走一走、看一看,说不定就能碰到如意“合伙人”。那年表姑去姑姑家,穿过小街,引得乡亲们啧啧赞叹:这姑娘真出挑,快说给咱村某某吧!后来真就成了。
小孩子们“出门子”想法就简单得多——蹭吃蹭喝、收压岁钱。那时,我最喜欢去的是二姨家。二姨家境好、孩子少,城里的亲戚又多,二姨还疼我,去了常常能吃到我家见不到的糕点、水果。初三一大早,姑且先抛弃“先走姑,后走姨”那一套,穿新衣、戴新帽,精心打扮一番,放上油炸果子,装上白面馍馍,背上红布罩顶的箢子,带上满满的诚意,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那个向往的小村出发了。
通往二姨家的路上,断断续续都是串门人,步行的、挑担的、骑自行车的。前面有个大哥拖家带口,全家出动,后座上载着媳妇,前梁上坐着孩子,车把上挂着皮包,按现在的话说,已严重“超载”。半路上,遇到赶牛车的一家子,拉了大半车箢子和包,看样子亲戚家是个大户人家。那个大哥邀请我把箢子放他车上,开始我不同意,怕混了。他猜出了我的心思,笑着说:“小伙子,箢子里有金蛋蛋吧!怕我掉包?”
转过三道弯,路过几片地,跨过一座桥,穿过一个村,依稀看到了上次暑假玩耍过的场院。草垛上,未化尽的残雪依稀可见,几只麻雀正在空地上觅食。穿过草垛,就看到了二姨家的大门,迈进去,正在择菜的二姨立马迎上来,热情地把我们领进屋里,端水递糖倒瓜子,嘴里连连说着:“快里面,快上炕,暖和暖和。”
当然也有个别素质低下的走亲戚者,一 言不合就耍酒疯、闹矛盾;也有厚此薄彼的长辈,压岁钱分配不均,惹得大人孩子都不高兴,我们村就有“出门子”吵架的,吵得不欢而散。
现如今,平日里物华天宝、流光溢彩,加之生活节奏变快、交通便利,人们通常丢下东西就走,也不谦让,履行程式般的“出门子”,少了些以往的仪式感,但也不可缺少。
□郭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