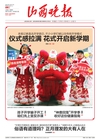取经传奇——两位文化学者笔下的高僧法显
法显研究在南京
我们说过,法显是山西的,也是中国的。这些年来,有关法显的研究不仅兴起于法显的故乡山西,也兴起在法显曾经走过的地方。例如青岛,也例如南京。
南京,六朝古都,文化名城,曾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而对于法显来说,南京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只说一条,法显携万卷经书东归之后,其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法显倾尽毕生精力翻译的那些经书,甚至包括那部伟大的自传《法显传》(《佛国记》)也是在这里完成的。法显与南京结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两点是不可或缺的。
其一,南京有个“道场寺”。
道场寺,位于今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外,始建于东晋太宁元年,而规划设计者乃是东晋名臣大司空谢石,所以又称谢司空寺或谢寺。有了这样一个背景,这个寺院或者说这个道场的规模层级之高阔,地位之崇盛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对于法显来说,以80岁的耄耋之年从遥远的南亚漂洋过海携经归国,此时他最想也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一个可以安放书桌、可以不受干扰地开展经书翻译的场所。而举目当时的东晋,道场寺无疑是最佳选择。
其二,在当时,整个东晋佛教界最具名望的佛学大师乃是法显同乡,其人名叫慧远。而慧远大师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几乎比肩法显。巧合的是,慧远大师不仅在年龄上与法显大师同庚,更兼两位大师又都是山西同乡。慧远(334-416年),山西雁门郡娄烦县岳茹村(今原平县)人。当法显远赴西天取经归来的时候,留在国内的慧远已经是名震江南首屈一指的佛学大师。其信众无数,弟子满门,而由他一手创建的庐山东林寺更是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著名发源地。应该说,对于法显西行的壮举,作为同道兼同乡,慧远一定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所以,当他听到法显东归之后,便不遗余力地呼唤这位仰慕已久的同乡尽快前往当时的东晋都城和文化中心建康(今南京)。为此,慧远甚至亲自来到道场寺,组织起在这里讲经学佛的僧人130多人迎接法显大师的到来,并在法显到达道场寺的当天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法显与慧远,两位同出山西的佛学大师,在这一刻实现了中国佛教史上一次伟大的会师。这样的故事,想想都是令人激动的无边画卷吧。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东晋义熙9年(413年)夏日,法显始一到达建康,便入住道场寺,并一住5年。也正是在这里,法显会同天竺高僧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了《摩珂僧祇律》《大般泥洹经》等得以流传后世的不朽经书,又以挤牙膏的精神,在翻译众多经书的同时完成了那部具有多重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自传体游记《佛国记》。而正因为法显的存在与他为佛教文化所做的贡献,道场寺的名声一时直上云霄,以不可撼动的地位成为和东林寺并峙的江南名刹。
从历史的角度看,法显对于南京的意义那就绝不止于佛教文化的传播与研究,这也正是在1600多年后的今天,南京乃至整个江苏学界和经济界都要对法显研究投以浓墨重彩的原因所在。这里,我们不妨引入一篇权威媒体“人民网”发表于2023年10月7日的文章《一路鲸波向海洋》。文章开笔气势宏大:“浩浩荡荡的长江注入浩瀚无垠的大海,水路之便催生出南京的自古繁华。”接下来,文章掀开了南京自古以来的开放史,而其中就有关于法显的重要描述:“公元399年,高僧法显从长安踏上陆上丝绸之路,历时十余载后又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南京,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首度在南京‘相拥’。在南京道场寺,须发皆白的法显,翻译出了等身的海外经典,也将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见闻写成《佛国记》。海外从未离开过南京的视线,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高潮悄然到来。”
这就是法显的价值,我们曾经说过,法显是真正的一带一路先行者,其光芒照耀着一带一路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
郭天印 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