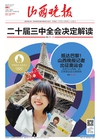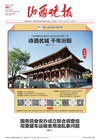老太原人夏日摆凉场
“小暑不算热,大暑在三伏。”三伏天是夏季里一段气温高又潮湿闷热的日子。此时老太原忙着换窗纱、铺凉席……以各种方式来应对炎热的天气。
西瓜是水果里消暑的佳品,盛夏都离不开它。以前没有冰箱,都是用自来水“冰镇”一会儿,有井水最佳,西瓜在冷水中静置一两个钟头。晚饭后,一家人边到屋外乘凉边分享“冰镇”西瓜。过去生活清贫,孩子常把西瓜啃到青皮还不住嘴,大人就会打趣说“吃到青岛了”,这“青岛”就是瓜皮。待睡觉时,大人就会把吃剩的西瓜皮收罗到洗菜盆里,到了第二天做饭时,去掉表皮及啃瓤部分,切丝凉拌,或者炒吃。特别是用红辣椒炒西瓜皮,是下粗粮的佳肴。西瓜籽则洗净后晒干,炒熟当零食,整个西瓜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凉粉是一道消暑的好食品。大院的人们多是自己制作,自家做的凉粉既是一道凉菜,也可使全家人敞开吃。大暑到来时,老太原人还讲究吃过水凉面,主要调料是用水澥开的芝麻酱,小料里葱花酱油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味特殊的调料,就是芥末酱。中午酷热,吃一碗凉津津、香喷喷的过水面,实在是享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太原人大多数都住在大杂院或小巷的平房里,那时候夏天热得出奇。白天,人们即使坐着不动,身上也会出很多汗。一家三代十几口人住里外套间的很普遍,晚上想冲个澡,是奢望。一些半大小子们干脆提上水桶,穿条短裤,赤膊搭毛巾,拖双木屐拉板儿涌向街头的公共自来水龙头,打上多半桶水,全身淋湿,再把肥皂抹在身上,互相用毛巾帮对方搓澡。也有的大人提溜上自个儿的小孩到水龙头跟前,举起水桶,从头上往下浇。别提多爽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老宅大院的住房是没有空调、电风扇的,逼仄的屋里热得不透气,在大院里纳凉便成了大家的共识。盛夏夜晚,邻居们都把自个家门前清扫干净,泼上清水,点把艾草,驱除蚊虫。随后,各家都把小饭桌、小板凳及躺椅一溜儿搬到各家门前,还有的支起木腿子搭几块木板,做成简易板床,摆上茶壶茶杯,有的干脆往地上铺一张旧竹篾凉席,端一碗绿豆汤盘腿坐在上面。于是有人称此情景为“大院摆‘凉场’”。
晚饭后,院里的男女老少开始群聊。上点年岁的男人们围坐在一起谝《三国》《水浒》,主妇们则三俩一伙地互相“秀”着手里的针线活儿,小孩则喜欢坐在老人的躺椅旁边,听故事。当然故事也不是天天都有,孩子们多半还是跟同龄人在一起玩。于是各家孩子将板床、小桌子当成舞台,彼此间赛唱、赛舞,被邻居们戏称为“板床舞台”。在板床上表演的多数是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将在幼儿园刚学到的歌舞拿出来在大人面前卖弄一下,常常引来院里的大人小孩欣赏。
当时最喜欢跳的歌舞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火车小司机》,各家孩子在各自“舞台”上比赛,免不了会因为比较而产生小矛盾,于是儿歌又变成:“你不跟我玩,我有人玩,我在河边划小船……”若是突然下雨,大家便火速撤回屋里,兴致未消的孩子们边唱着:“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嘻嘻哈哈各回各家了。
遥想大杂院里的那些夏日,绿豆汤甜,凉茶泡酽,蒲扇来风,苇席吸热,谈古论今……相比如今在沉闷的空调屋里死盯着手机屏幕惬意多了。
除了吃凉瓜、凉面或冲澡等消暑方式,有的老太原人还会迎热而上,以热祛热。小店、晋源一带的乡村人家讲究在大热天喝羊肉牺汤,据说可以趁天热补气理中。而城里大杂院的人家讲究:“头伏饺子二伏面。”他们认为,在闷热的三伏天里,热腾腾地吃上一碗饺子或面条,吃得大汗淋漓,可以帮助身体排毒,也能调节体温。还有的老人会选择阳光热烈的时候“晒背”,也是老太原人伏天的一种养生方式吧。
支蚊帐、挂竹帘、搭凉棚……钱稍富余的给孩子抹点清凉油、擦点痱子粉。大杂院的人们就是用这种简单又实用的方法,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为自己营造出了一种舒适凉爽的生活环境。
彭庆东(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