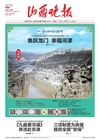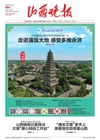流淌在我心中的河
我出生在太谷乌马河上游的一个小村子——杨庄。年过八旬,又是病中,时常会梦到或想起生我养我的地方。二女儿告诉我,她的好友写了一本《黑马河》,就是以杨庄为原型,主角就是在村里当过第一书记的杨川宝……得知是我的故乡,作者周俊芳专门赠我一本,在扉页上写了两句话,让我很感动。
翻开书,开头再现了2015年8月12日乡政府送驻村工作的第一书记到各村的情形。看着,看着,这不就是原来我们窑子头公社(现属阳邑乡)的十几个村庄?黑马河不就是流经我们村的乌马河?各村的基本情况、环境人物、说话的习惯,都是那么熟悉。因为写得很生动,让我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家乡的风土人情浮现在字里行间,打开书,我就感觉回到了故乡。尽管老眼昏花,体力不支,没用几天,我还是把这本书看完了。《黑马河》勾起了我对家乡的好多回忆,并产生了很多感慨。
乌马河是太谷的母亲河,就从我家窑洞下方的大堰底穿流而过,大堰底高出河床二十米左右,河床有四五十米宽,对面是石崖,乌马河常年累月哗哗流淌。山坡上的杨庄紧靠乌马河,可吃水还是很困难。吃水都是从乌马河去挑,挑水很费力,需要走很陡的坡。
洗衣服要到河里,把洗的衣服浸在水里,用石头压着,不然就会被水流冲走,水流淌会帮我们把衣服预冲洗,河里水宽,洗的衣服干净一些。洗一件,就在河床的大石头上晒一件。河岸边那块大大的巨石不知道是何年何月被洪水冲下来的,高有两米多,周边有四米多。那是村里人晒衣服的好地方。
乌马河安静的时候水清凌凌的,水里鱼儿在水草间游来游去;有时河岸上还会有乌龟在河滩上悠闲地爬行。乌马河边绿草野花好美,此时的乌马河像温柔的母亲。
到了麦收季节,有时乌马河会突然变得很暴躁,瓢泼大雨来临时,滚滚的洪水就会咆哮而来。水面会漂浮着纠缠在一起的大小树枝、大小石头,还有各种瓜果。河宽从十几米一下子扩展到几十米,乌马河东支流、西支流一起奔腾而来,挨近河的地被冲垮,农作物被无情地卷走。此时的乌马河,像不讲道理的、咆哮的父亲!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会玩水的弄潮儿,会在发大水的时候,玩命似地打捞起从上游漂浮过来的东西,不会水的在这个时候最难熬,发怒的河水把他们辛苦栽种的作物一下子夺走了。
乌马河发脾气最盛的时候,已经不是不讲理了,它会吃人。我印象深刻的就有几次,此时的乌马河泥沙俱下,如面目狰狞的魔鬼。
冬天的乌马河是白色的,孩子们在结冰的河岸上,有的坐着冰车玩耍,有的站在冰上用脚发力滑来滑去,这时的乌马河是孩儿们欢乐的场地。
乌马河就这样流淌在故乡小村旁,我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出生、埋葬,静听着乌马河流淌的声音。这条蜿蜒的河,流淌着我们许许多多的往事,河水也伴随着时光,流向远方。
我是1963年从汾阳师范毕业,分配回窑子头公社联区教学。那时每个村子都有小学,由师范毕业的专职老师复式教学,我们一帮年轻人奔波在家乡深山里的各个小学校。
乌马河水的两股支流,水源充足得很,我们村利用有利条件建了水磨房。到1980年,几乎全是水地,坡地用抽水机也能浇上,各种粮食作物都能种,西红柿、黄瓜、豆角、茄子、西瓜、南瓜,一筐筐分回家。深秋,苹果、梨、核桃、山楂出现在山坡地边上。一进村,你去看吧,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是树,尤其苹果树上一串串红红的果实,把树枝都压到地上了,果香扑鼻……
可不知什么时候,乌马河的水流渐渐地小了,都能看见河床了。村里的小学和卫生所搬到阳邑,年轻人为了孩子上学陆续搬离村子。果树无人照管,梯田变成荒坡,只有留守的老人寂寞地坐在村头,晒着太阳。书中第一书记刚进村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吧。
这一带山区是抗战革命老区,村村通油路、通电,用上了自来水,但是村里人越来越少,所以上级派去第一书记解决实际问题,是党的好政策支持农村富起来、好起来。第一书记不怕苦、不怕累,真心实意地投入到农村,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建设美丽新乡村。
我相信会有很多像杨书记这样的党员干部,为农村发展殚精竭虑。合上《黑马河》,乌马河水静静地流淌进我心里,哗哗的水声回响耳畔,如此清晰,许多回忆次第浮现,故乡故人,永难忘。
□杨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