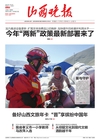坐闷罐车回老家过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乘火车回老家过年,结果原来的客运车厢调到了其它线路上,临时用闷罐车替代运送旅客,我们只能坐闷罐车回老家了,印象深刻。
老家在北同蒲铁路东侧,从太原乘火车到定襄站下车,离爷爷家的村仅有10里地。父亲说,春节要回老家过年,我们高兴了好几天。那些天,最忙的要数妈妈了,给我们准备过年的衣服,从省城回老家,要尽量穿戴得好一些,让爷爷奶奶感到我们在外的日子过得不错。我是家里老大,妈妈给我赶做了身新衣服,弟弟们穿哥哥们退下来的衣服,尽量补丁少一些,合身得体。
父亲要忙着买一些点心,拿上十来斤我们平时省下的白面和大米,老家缺白面,没大米,给爷爷奶奶吃个稀罕。还要带上些好酱油醋,奶奶也酿醋,但口感色泽比太原产的差远了。年货置办好了,就要去正太街的太原火车站买车票。
到了火车站,排了两三个小时的队,到了售票窗口,年前的火车票还有,就是闷罐车。闷罐车也叫盖车,是货运车,春运客车不够用,闷罐车就当客车用了。父亲就只能买闷罐车的车票了,好在车票价格比客车票要便宜,也是一种安慰。
早晨7点多火车开车,5点来钟,妈妈就做好了饭,吆喝我们起炕。洗了脸,吃了饭,天还黑黢黢的,我们就背上大大小小的行囊出门了。家住桥东街,离车站不远,一会儿就到了。我们在车站广场的冷冽寒风中排起了长队,准备进站。
过了检票口,连跑带走,急急忙忙找见了我们的车厢。闷罐车的车厢里黑乎乎的,墙和地板都是木质的,中间两扇门对开,可以推拉,门前也没有台阶,我根本爬不上去。父亲把我抱上去,而后把东西递到车上,我们接着,拖到门口旁边,父亲才趴在车门口翻上来。
车上没有桌椅,地上铺层蓆子,离车顶不远的地方,开着一溜一尺见方的窗口,车顶上有个灯泡,但并不亮堂。车厢里用一个铁火炉子取暖,并不感觉暖和。车开了,车厢里有一百来人,坐得满地都是。父亲让我们就地坐下,怕我们摔倒。但天性好玩的孩子们又哪能闲得住,稍不注意,我们就溜出去玩一会。车内没有厕所,只有到了车站,才能下去解个手。到了忻州站停得时间长,我们还下去稍微活动一下,舒解一下坐在地板上困乏的腰腿。
列车行驶了4个来小时,到了定襄站,下了车,叔叔早已等在站台上。叔叔用自行车带上年货,我们步行,快到村口,远远看到奶奶家冒出的炊烟。一阵兴奋,早已忘记了坐闷罐车的困乏。
现在我们再回老家,方便多了,高速一个多小时就到家门口了,恍如隔世啊。
梁建军(太原)